剧集“开年第一会”复盘:在“长短”之间探索好内容落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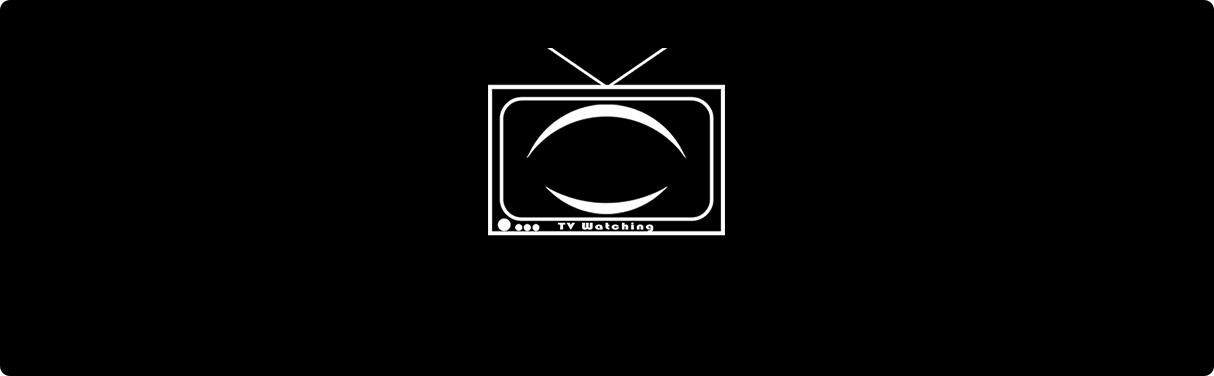
文 | 芷潇
来源 | 看电视
2月20—21日,被称为影视行业“开年第一会”的首届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大会暨第十届中国(深圳)国际电视剧节目交易会在深圳举行。
历时两天,大会输出了密集的先锋洞见。来自各大平台的领军人物,分别结合前瞻数据、业务实践和独到观察,向行业传递敏锐的市场信号,共商剧集转型期的破局之道。
14场专业论坛,话题覆盖了产业趋势、技术革新、海外市场拓展等行业热点议题:有对AI利好的乐观展望,亦有对技术艺术边界的感知探源;有资深从业者面对短剧冲击的前景预测,亦有行业新秀对商业模式的公开解密……
无论是长视频平台集中爆发的进化危机,还是微短剧运营越发成熟的流量逻辑,本场行业大会所谈论的重心,均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内容的质与形,模式的优与劣,以及剧集工业体系的迭代与进化。
感知、激辩、呼吁、预见。“长短之争”的背后,是聚焦内容表达的核心诉求;观点碰撞的隐喻,是从业者对良性市场竞争机制的呼唤。“开年第一会”已落幕,值得记住的远不止是一次控诉和一场争辩。

内容的质与形:
从“长短之争”转向“表达之需”
“微短剧盛行,如何避免观众对长剧情耐心下降?”“长剧集有没有必要向短剧集体迁徙?”“短视频时代,长剧如何生存?”……
毋庸置疑,在多平台时代的竞争压力下,传统长剧制作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生产规模受到压缩,盈利空间持续收窄等多重困境,让“长短之争”成为今年大会聚焦的首要话题。
早在2月20日“迎接‘剧’变,变与不变”的主题演讲中,中制协会长、制片人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侯鸿亮就曾提到,“剧集长短应服于叙事,用品质定义精品”。尽管微短剧符合现代观众的快节奏需求,但其内容深度和创作质量依然面临挑战,许多作品缺乏深刻性,陷入套路化和同质化困境。
著名长剧导演郑晓龙亦对微短剧的强势爆发表达了忧虑,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不应仅仅满足娱乐化需求,而应兼具深度和广度,既能让观众获得娱乐体验,又能启发他们对社会、人生、历史等更深层次的思考”。
根据红果短剧总编辑乐力给出的数据,尽管微短剧创作还未能成熟地平衡好严肃性与娱乐性之间的关系,但整个微短剧用户观时长已经接近整个视频故事赛道用户观看时长的一半。

一边是长剧行业提质增量、产能下降,一边是微短剧高速增长的内容预算,长剧集是否有必要向短剧集体迁徙,成为了风口之上的选择性命题。在21日的论坛上,著名编剧汪海林、、白一骢、余飞等就长短剧内容质量、创作方法和未来发展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首先是论坛议题设置的合理性。
汪海林认为,“短不代表天然的先进性,长和短就是篇幅的区别,而不是说短取代长已成为社会趋势。”他以春节档电影平均时长上调为例,指出观众失去耐心、弃剧率高、包括长视频平台会员流失的原因不在于“长”,而在于质量平庸。仅仅着眼于篇幅来破题,并未真正涉及问题的核心。
而在郭靖宇看来,长剧跟短剧在本质上都是讲故事的艺术,二者之间没有对立。编剧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故事具有更有高的陪伴价值和传承性,而非只停留在短效的周期回报。就形式上而言,郭靖宇主张发展结合了微短剧优势的“中剧”,通过对盈利模式进行完善,挣有想象力、被资本看好的钱。
其次,“长短之争”还表现在商业潮流下从业者身份意义的错位。
白一骢以亲身经历揭露短剧行业乱象,“微短剧编剧在劳动上被拼命压榨,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要求按照公式、套路去做。《当山花烂漫时霸道总裁来到我身边》这般的短剧篇名,除非是薪资丰厚,否则是很难放在代表作品里让别人去阐述的。”

横亘在长短剧接壤之间的问题是,两者在商品性和艺术性上各执一端。 这并非是想说明长剧普遍拥有过硬的作品质量,而是相较于投流机制下被泛滥翻拍和套路化创作的短剧而言,编剧这一传统影视工种的价值锚定是被动摇和轻视的。
体量篇幅之长短,是剧集的“形”,而真正能唤醒观众的生命体验、留住观众视线的,关键还在于剧集的“质”。如果说无限重复、占据时长、煽动情绪,是短视频的叙事三部曲,那么急迫转型需求之下,“长剧向短”的探索与坚守,将勾勒出行业转型升级的未来路径。
模式的优与劣:
如何营造良性市场竞争环境?
“特别是有些平台利用市场的主导地位,签一些排他性的协议,跟他合作就不能和其他的平台合作……这件事非常糟糕。 ”
2月20日,爱奇艺创始人、CEO龚宇用非常严肃的措辞,针对红果通过与版权方签署排他性协议的形式垄断产能的举措,进行了点名控诉,并且引发了行业内外的热烈讨论。
事实上,版权归属、产品议价、内容交易等,一直是剧集产业关注的重点话题。早在2016年前后,互联网平台就曾上演拼内容价格、砸钱抢资源的先例,彼时对于重点IP的版权争夺战,更是将《如懿传》单集炒上了天价片酬。

现如今,视听产品迭代,新一轮内容抢夺战打响,平台内卷的方式也有所变化。长视频平台刚就短剧赛道开始囤粮布局,就被红果以更彻底的垄断性合作模式腰斩。当短剧制作方不再具备作品的议价能力和播出平台选择权,这对于行业的未来发展必然是有消极影响的。就这个层面来看,爱奇艺的直言不讳,具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新事物在发展初期,总有野蛮生长的阶段,更何况是在技术持续介入影视产业的当下。除了这场“喊话”,本届大会还对“如何营造良性市场竞争环境”的问题,进行了各方位的探讨,覆盖AI创作版权归属、制片公司舆情风控等多个方面。
其中,“AIGC如何贯穿剧集制作”主题论坛结合降本增效,对剧集生产全链条进行了拆解和赋能方式解说。目前,可灵、MIMO、Deep seek、海螺AI已被运用进视听作品的制作领域,包括运用AI进行信息提取、评估分析、虚拟拍摄、选角推荐等等,但其投喂数据的风险性和侵权隐患还需法律条款进一步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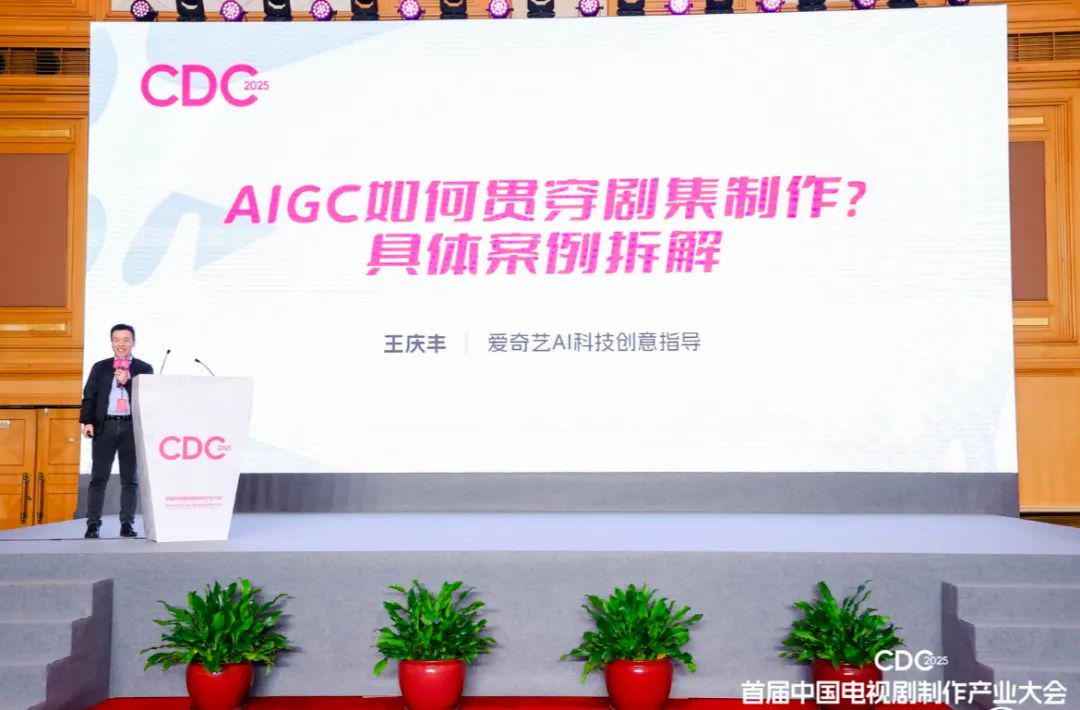
关于AI大模型生成素材的版权归属问题,可灵AI产品运营负责人王若暄如此回应,“所有物料都首先由平台确保拥有明确的、合法合规的版权来源,另外,项目合作环节也会提前约定好版权归属条款。更重要的是,著作权和版权保护的是创意本身,而不是受限于一个工具,对原素材多次修改的过程,是大家维护自己著作权的有力证据。 ”
舆情风控方面,律师王军的“影视项目的法律和财税避坑实务”专题分享同样干货满满。
他指出,影视行业的舆论聚焦和公众传播属性,让影视剧作品在制播环节的隐患排查变得至关重要。面对“一般的问题复杂化,社会事件意识形态化”的舆论环境,签订演员聘用合同中的“艺德条款”、引入内容合规审查顾问、合理核定版权剩余价值,是保障和挽回相关权益的重要措施,值得从业人员重点关注。
有机遇亦有挑战,要高歌猛进也要规避风险,无论是对AIGC的版权归属讨论,还是爱奇艺对红果的公开发问,本质上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既蓬勃发展又良性有序的市场模式,在健康竞争环境下更好保障各方权益。问题暴露的节点,也正是步伐调整的新起点。
剧集工业体系的迭代与进化
经过了前期造势、探索应用与项目落地,AIGC之于影视创作,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2月21日,以《三体》《唐朝诡事录》为案例,“AIGC革新影视创作”主题论坛向从业者介绍了技术实操的成功应用和切实挑战。
其中,导演郭靖宇提到,“特效能不能帮助做讲故事,这是特效第一重要的任务”。他以《唐朝诡事录》中《千重渡》一章的制作过程为例,重演了创作者在志怪题材想象过程中的细节和难点,“从编剧的角度上来讲,最重要的是你赋予它的行动是否能够完成”。
嘉宾张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补充,“视听艺术具有内容的宽容度和技术的融合度两大特征,因此算法、数据、算力的提升和大模型的国有化替代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在实操环节常出现的问题是,创作者在给出指令之前缺少构想的过程。好的决策能力和融合能力才是用好AI的关键。”

另一边,“虚拟拍摄到底怎么做?”主题论坛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更深入,也更细分。在过往经验中,虚拟拍摄准备周期长、成本高,是专属于大预算大项目的噱头。但当AIGC对影视产业的渗透程度再进化,这一看法是否还有效?
爱奇艺副总裁朱梁表示,目前来看,“头部平台以及头部IP用虚拟拍摄、数字资产的复用方式,大大提升了质量和效率。虚拟制作还是要付出一些成本,但它肯定不是一个超级效果才有的专利。”
当突破了第一步基础建设,后续资产库便可以在生态体系中完成复用,比如做好的场景资产、服装资产、空镜、道具、生成式AI的模型等等,不仅是在单一平台项目中的流通使用,随着应用场景越来越多,这些数字资产能够在版权明确的基础上,打通平台壁垒。
腾讯视频影视内容制作部高级总监金瑜以《待我醒来时》为例,具体拆解了制作成本的节省效率,无论是前期置景还是后期制作时间,都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包括工作前置化这一模式,能够进一步降低现场工作强度,提高实操的可能性。

在技术与艺术的边缘,AIGC赋能剧集工业体系迭代正处进行时。但无论如何,诚如龚宇在演讲中所提到的,“集数、时长规格、IP、演员流量、成本、AI、虚拍等现有问题不是最重要的,观众喜欢最重要”。
“长短之争”的新困局,未尝不是剧集行业“长短共荣”的新机遇;商业模式的探索与试错,未尝不是一个良好剧集生态的前奏;而技术与艺术争辩,也未尝不可走向“人之为人”、科技向善的理想落点。让我们保持期待,迎接注定不平凡的202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