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童年⑫丨伍姿:童年的风筝 你好童年威海 你好童年你好时光画展

童年的风筝
文/伍姿
前段时间,异国的好友在机缘巧合下得了一只风筝。她第一时间便打了视频过来炫耀,红色的条形风筝几乎占据了整个屏幕。黑色的线条在纸背上肆意延伸,勾勒出一个抽象的图案。好友得意洋洋地介绍,那是一只龙。我努力辨认,终于在她的介绍下分清了龙首与龙身。
英国的天似乎总是阴沉沉的,浅淡的云彩轻轻飘过,不留痕迹。在高大的钟楼旁,渐渐升空的风筝,成为灰蓝底色下的唯一的明艳。纤细的绳拴着它,肉眼已看不清风筝上的线条,恍惚间好像真的有一条红龙在异国的天空自由翱翔。
与好友闲聊着,便回忆起往昔。
我们的童年似乎都与风筝有关。
已忘却第一只风筝究竟是何时得到的了,只在记忆的角落中找到一丁点关于它的痕迹。
那是一只燕子形状的风筝,颜色很艳丽,红的红,绿的绿,黑的黑,每一个部分都泾渭分明,头是头,身子是身子,尾巴是尾巴,绝对说不上好看。然而就是这样一只可以称得上“丑陋”的风筝,竟不可思议地得到了孩童时期的我的喜爱。城市中的高楼一栋接着一栋升起,渐渐霸占了整片天空。在拥挤的高楼间很难找到一片足够广阔的地方容纳风筝,于是回到乡下的老家,便成为了一种可以肆意奔跑放飞风筝的代名词。
那时候回到老家还要坐大巴车,可四个小时的旅途对孩子来说实在太长。坐在座位上,东扭扭,西看看,什么都觉得有趣,拉拉靠背上的扶手,摸摸束起来的窗帘。可玩了半天,前方还是看不见尽头、一成不变的灰色柏油马路,就觉得无聊起来。但一碗泡面足以打发我,大巴车上的水实在不是很烫,面饼还带着未完全舒展开来的硬挺,然而稀里呼噜吃下肚子后,却觉得实在满足。摸着微微鼓起的肚子,在小船般的晃晃悠悠中,合上眼皮了。再一睁眼,发现发动机的轰鸣已经停止。四个小时的旅途,实在是太快了。
在放飞风筝之前的等待实在煎熬,屁股下的板凳似乎变成了一块滚烫的烙铁,烫得人坐立不安。只等妈妈一个允许的眼神,身子便冲了出去。外婆的叮嘱还在空中飘荡着,然而被殷切嘱咐着的小人儿已拖着风筝,在田埂间奔跑起来。鲜艳的燕子风筝跌跌撞撞在身后挣扎,就是飞不起来。我在伯伯婶婶的笑声中气喘吁吁地停下,回头望见风筝的周围都糊上了褐色的土块,赶忙捡起来,想将上面的泥巴拍掉。意识到徒劳的举动后,我丧气地垂下头。一位婶婶停下劳作的锄头,走过来帮我。她的袖口挽到手肘,露出棕褐色的手臂,显得很长、很有力量。风筝被她高高举起,很快,我再次奔跑起来,风筝这次乘着风,悠悠飞上天空。
飞咯——
在我的欢呼声中,燕子风筝飞得很高很高,只剩下一团模糊不清的色块。摇摇晃晃的风筝,似乎下一秒就要挣脱细线的束缚。
风大了。
啪。
线断了。
燕子真正飞上了天。
后来拥有许多风筝,却都比不上那只飞走的燕子。有一次,姑父告诉我,他会做非常漂亮的风筝,让我等着他,他去买材料。我便等在老家的院子里,从清晨等到太阳落山,连晚饭也是端着碗坐在路边吃的,因为我想第一时间发现那条小路上浮现的人影。外公无情地嘲讽了我的天真,让我别等了,进屋去吧,我执拗地蹲在原地,等待着、等待着……直到姑妈与姑父分开,她哭着对所有人说那个男人是个骗子,倾述自己受到的伤害。是的,我在心里默默点头,我的风筝永远等不来了。
弟弟的童年应当与我是不大一样的。对我而言,放风筝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而他在体验过几次后,便宁愿选择待在房间里打上两把游戏。有一次,我发现他不再打从前那个游戏了,因为他们班的同学不玩,他体会到了无人分享的孤独,于是转而玩起了另一个大火的游戏。游戏对于他来说,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方式,更是一种合群的方式。我们相差十一岁,有时候会觉得年龄差确实带来了一些距离感,有时候又能够与他感同身受。比如,放风筝这件事上,也在无人陪伴的寂寞中,渐渐不带有吸引力了。连带着乡下的风景,也变得无趣起来。我常常怀念自己的童心,却怎么也无法想起了,大概我也成为一个“合格”的大人了吧。
断线的风筝,谎言的风筝,寂寞的风筝,都伴随着童年,渐渐隐去了。
作者简介:伍姿,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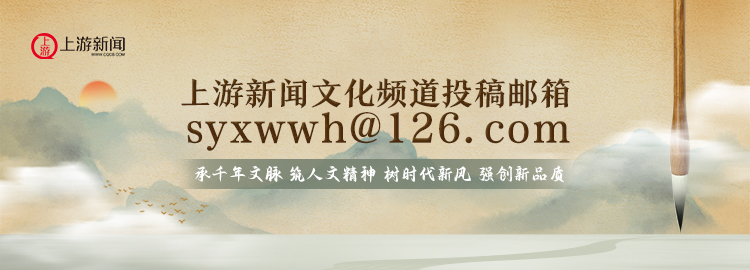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