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丨李之邨:河边的磨坊与山林(组诗) 缙云丨李之邨:河边的磨坊与山林(组诗)

河边的磨坊与山林(组诗)
文/李之邨

河边的水车磨坊与红鬃马

凝视深壕里这架咿呀转动的水车
只过了几分钟
我脚下的大地便开始发软开始眩晕
哗哗的水声中,喝醉的水车扶着爬满
青苔的石壁,大口大口地呕吐
不断地甩锅,拒绝承受任何流水之重
水车吐得满脸发绿,磨坊那具沉重的石碾
反而吱吱呀呀地转得越欢,碾过一圈
又一圈,让新米的味道香遍河岸

举重若轻的水车,公子哥儿似地
只负责喝酒负责喝醉了呕吐
实沉的石碾,只管和环形的磨槽较劲
这俩口子经常拌嘴,吵得水花与谷壳飞溅
吵得磨坊的地皮微微颤抖,而架在深壕的
木轴,暗中使劲,它却说它一向保持中立

缺水的季节也是青黄不接的季节
水车停转,人们却急需把陈谷子碾成白米
一匹毛色发亮的红鬃马,便来代替水车
它一个劲拉着石碾转圈,居然不晕头
那块蒙着双眼、让它看不见前程的黑布
一定是一块神奇的飞毯,陶醉了红鬃马
让它以为自己一直奔驰在无边的草原
人类是怎样想出这个小小的诡计
怎样知道蒙上马眼,马就能一直转圈
而人们蒙着双眼转上几圈,只会一头栽倒
因为这块小小的黑布,和这间河边的磨坊
我从此对古老的山野满怀敬畏和好奇
它有着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神秘

翻新古老的山野

我经常诧异,㤞异于给一些更加年轻者
讲述仅仅几十年前的旧事,犹如讲述
古代的异国历史
令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穿着长衫
赊了酒站着喝的迂夫子,脑后有根辫子

但是当我们一起回忆摇着木铎的采诗官
泰戈尔的森林大学,闻一多的露天学校
杰克·伦敦怎样飞上火车当了丐帮帮主
我发现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话语
接下来我说我曾穿过百里无人的森林
我听到过地底传出恐怖游移的低嚎
我看见过无头无尾、会飞弹的撩棒蛇
他们的双眸开始燃烧远古崇拜的火苗
我懂了,要旧,干脆就旧得彻底
旧得极度原始,旧得茹毛饮血
以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的比例
以不怕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勇气
把田野放还于山野,舒枝展叶
至少要放还七天

秋凉后场坝上的戏台子

秋粮入库到大雪纷飞之前,天气凉爽
积攒的时间盆满钵满,大把大把地花不完
此时最适合唱戏,适合疯传家长里短
适合慢慢拨弄算盘
适合晚饭后坐在屋檐下发呆
散漫的目光在一块块青石板上打滑
适合烂醉如泥,打着飘走路
有家不归,倒在街边打鼾

晚上,喧天的锣鼓擂响千百张挞斗
人们一个个被戏台扯长了鸭脖子
乔装打扮的草台戏班看上去很有档次
那些黄袍凤冠金盔银甲长衣短衫
几千年的各色衣装,同台拂袖宛转
刚刚三国,倏忽唐宋,又回秦汉
人们因此知道了汴京沧州洛阳长安
同时觉得老街四周一座座大山
也跟戏中的长坂坡马嵬坡差不多
唐明皇也有坐在路边啃大饼的时候
人们一边叹息,一边也有些几分释然
何苦明枪暗箭,不如做一个庄稼汉
方圆百里之内,这个独一无二的戏台子
端坐在四乡八寨唯一的场坝上
时不时把人们托上肩膀,打望云山

夜行于一片噪鸣的山谷

山野已是黄昏,从不刷牙的石缝
塞满老黄的蟋蟀和发绿的草叶
草丛和灌木都在不厌其烦地噪鸣
一个劲炫耀它们小小的巢穴
衬托我归家之路的遥遥无期
每一次蛙鸣的停顿,都在暴露
我的行踪,月光的探照灯追着我
让我脸上盖满金印
每一步都像惊弓之鸟的逃亡
身后全是追兵,背上都是冷汗
耳边隐隐约约,都是呐喊

迎面扑来的黝黑松林,并非要
和我亲近,而是要与我贴身肉搏
深夜的喧闹从来不属于人类
火把下赶路的人们都懂得默不作声
此时敢于唱歌哼小曲的,只有
聊斋里的狐妖、僵尸和鬼魅
每一个分岔的路口吐着蛇信
诱使我嘴里发出咝咝的响声
以夜游蛇的姿态和山路一起蜿蜒

在深山老林中

深山老林是甘于默默无闻
有没有诗意都可以栖居的底线
不像那些无人的荒漠与戈壁
只允许我们匆匆地走过
美中不足的是在山林里呆得太久
眼神可能会渐渐发绿,说话会
带着咆哮、会忍不住粗声大气
会以虎豹和鹰的眼神打量世界
柔弱的泉水和溪水会越来越硬
会仗着高耸入云的山峰和森林
否定不属于山林的一切

因为蛮荒的山林大度地容纳炊烟
容纳小路容纳人们歪歪扭扭的足迹
浑厚的鸟巢宽容卧榻之下的茅屋
锄头扁担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一忍再忍,忍了几千年
我们必须以攀登理解山峦的高耸
以友善理解排斥警惕的眼神
以汗水理解弥漫山林的泥草味

作者简介:李之邨,本名龚炜,重庆市作协会员,曾任教于重庆交通大学旅游与传媒学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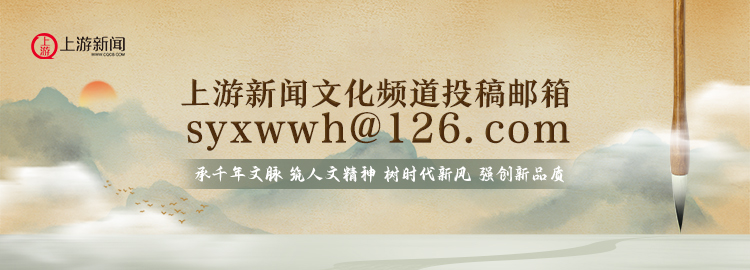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