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丨林檎:啖鱼史 推荐丨林檎:啖鱼史 林檎适合什么人食

啖鱼史
文/林檎
老莫渔档没有点菜一说。后院就是鱼塘,里头什么玩意儿都有,鲢、鳙、翘嘴、老鳖甚至小龙虾,钓上啥吃啥,全凭运气。不知道刘总为什么请在这么个地方。我虽算不得什么老饕,从凉拌大板鲫到金枪鱼刺身,倒也是吃鱼无数,我不相信这么一个乡野渔档能有什么人间至味。有钱人就是吃饱了撑的,花钱买罪受。凭我如何抱怨,刘总依旧在后备箱捣腾渔具。晾了我得有五分钟,末了递过来一根鱼竿。抓紧时间吧,他说,天黑之前没有渔获,咱可就白跑一趟了。
说起来这顿鱼约了个把月了,那会儿我跟刘总刚认识。同在一个渔友群,就数我俩技术烂,参加过几次线下比赛,让人家发现是滥竽充数,都不愿带我们玩儿。一来二去,我和他倒成了难兄难弟,谁找到钓鱼的好地方,都要喊着玩儿一趟,不为渔获,单冲着晚上那顿酒。 酒足饭饱,回头再上菜市场买两条草鱼拎回家,也能跟老婆交差。本地吃鱼倒是没啥讲究,除了蒸就是烤,不出俩月我们已经吃遍江城六区四县,聚会一度因此中断,直到两个小时前刘总又来电话。电话里刘总只说是农家自助,听着怪有意思,没想到是这么个“自助”法儿。拎着网兜跟在刘总屁股后面,穿过一片稀疏的菜地就是鱼塘,塘边用石棉瓦搭成两排凉棚,棚下荫凉地里立一个人影儿。刘总上前一步给我介绍:老莫,莫老板、莫大厨,都是他。抬眼望去,棚下逆光,瞧不清细致模样,但可以确定,老莫一点不“老”。穿格子衫,瘦高个儿,戴副黑框眼镜,一副学生模样,再准确点讲,像个程序员或者研究生。我拎着钓鱼的装备没法伸手,不过对方也没有打招呼的意思,不知道跟刘总嘀咕了句什么,扭头就跑了。有点意思,我问刘总,你从哪知道的这地方?网上,逛论坛遇到的。刘总插好炮台,支起小马扎,回头跟我说,瞧着像那么回事儿,就给你去电话了。有人说是子承父业,家传的烹鱼手艺;也有人说是高才生回乡创业,有机鱼塘,肉质鲜美无比。反正吃过的都说好,鱼好,人也够意思,喝到位了能聊半宿,临走还给你免个单。你们报社不正在搞人物访谈?“发展养殖餐饮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这多好的素材。李白斗酒诗百篇,说不定吃顿鱼的工夫,你这文章就出来了。我说你想得还挺远,先把鱼钓上来再说吧。说完我也开始挂钩,就我和刘总这技术,能不能吃到鱼还两说。正要抛竿,一枚鱼饵抢先入水,我还在想刘总的动作什么时候这么熟练呢,扭头一看,不是他,是老莫,鱼档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
你俩是新手吧。他早已看出我们的斤两,说,反正下午没人,我给你们添一根杆子,增加上钩概率。免得到点儿钓不到鱼,白收你们二百块钱,多不好意思。年纪不大,口气不小,我说你想过手瘾就直说,都是钓友,犯不着你可怜。没想到那小子把头摇得像波浪上的鱼漂,我没这爱好,一坐坐一天的有什么意思?他说,我讨厌鱼,讨厌关于鱼的一切。我原本打算卖完这塘鱼就离开江城,都怪你们钓鱼的技术不行,几年下来鱼没钓到多少,投下去的饵料反倒壮大了水族种群,我这生意越来越红火。可能是老爹不想让我走吧。
这小子越说越得意,刘总看不下去了。你少扯淡,他指明要害,真想卖鱼,拿网抄不就得了?一网打尽,鱼鳖虾蟹都跑不了。可是抓哪条不抓哪条呢?小伙子反问,这是我爹留下来的鱼,我没权力决定它们的命运。不过它们自己咬钩,我就管不了了。我差点没忍住笑出来,这年头不懂点哲学都不敢卖鱼了,刘总说不赢他还真不冤。我上前解围,说鱼怎么想的咱不知道,你爹就不一样了,他想你留江城也是为你好嘛。歌词怎么唱来着,“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我问刘总,下句是啥?安稳,老辈儿就是求个安稳,刘总回答,你们年轻人体会不到,这东西跟烟酒茶是一个道理,初入口都觉得滋味不好。到我们这岁数你就明白了,钓鱼,比什么都好。可能是吧。看来高才生吃这一套,他听进去了,点点头说,我爹也喜欢钓鱼,你们能说到一块儿去。他要是在你们准能喝两口。刘总把大腿一拍,扳回一城。他乘胜追击,说也别准不准的了,择日不如撞日,我后备箱带着酒水呢,快给老爷子打电话吧。这次对面没接茬,你们来晚了,他顿了顿说,我爹死七八年了。
我看了眼手腕子,午后三点,正是热的时候。四下里无风,水塘一片死寂,想不到找补的话来说,偏偏鱼漂也懒得动弹。看来真是没什么生意,渔档老板干脆捡了个马扎在我们旁边坐下。无处可躲,我们老老实实等待老莫开口,如同等待审判——
在我俩三十年的人生交集之中,老爹几乎总是跟鱼一起出现的。
渔档老板把手竿插进炮台,从头开始讲起:我莫仕图这辈子吃的第一口食儿,就是我爹喂的鱼。那时候我刚从卫生院抱回来,屁股还没沾床,我爹就端着汤碗过来了。看见媳妇把儿子的脑袋往怀里塞,他就知道大事不好,赶在我咬上奶之前,一只手把我的脑袋扭了过来。当时我的颅囟尚未合拢,因此整个脑瓜子被他捏得细长。我妈从未想过一个母亲喂奶的权利会被自己的丈夫剥夺——但凡娘胎里出来的东西,哪有开口不吃奶的道理?可是我爹不为所动,他从汤碗里挑中一条小鱼,俩指头拈住尾巴提溜起来。现在我当然知道,那是江城特产黄辣丁,炖汤滋补的好东西,三条鱼,一瓢水,半块豆腐,满屋子鱼香。可惜这品种现在全靠人工育苗,激素催肥,滋味全无。我这儿的不一样,钓鱼佬舍得花钱,打窝都用豆粕、苞谷,纯粮食喂养,膘肥体壮,最宜炖汤。只要你们运气好能钓上来,晚上我可以做酸汤鱼……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刘总听不下去了,扭头跟我嘀咕。我赶紧拿胳膊肘杵他,谁让咱说错话?为死者讳嘛。不知老莫听没听到,可能想想是这个道理,便就此打住,说回老爹:
老爹当年喂我的肯定是地道野生黄辣丁,那股子鱼腥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呱呱落地的孩子,没有哪个不哭不嚎,只有莫家,不论男娃女娃,一见鱼就笑,有鱼吃就乖。我盯死老爹手中汤碗,远远地闻着味就乐呵起来,两只小爪子扑棱不止,揪住鱼翅膀就把那黄辣丁整条吸到喉咙里。我爹倒也不担心,他只是拽着尾鳍,防止我被噎死。只听见我喉管里咕噜咕噜攒动不停,等到半支烟的工夫,我爹说一声好了,就把鱼尾巴一扯——那小鱼方才是全须全尾地进去,现在又完完整整地出来,连根鱼胡子也没少。我爹心头一惊,立刻明白怎么回事。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声响动:吧唧。鱼摔在地上,我爹把我妈扑倒在床上。他几乎可以断定,我不是他的种,我不是莫家的后。
鸟雀出壳就会叫,骡马下地就能跑,莫家的种咋能没有天生吃鱼的本事?宗族旧例,莫氏添丁,头一口吃鱼,祖宗八辈没出过差池,咋就这小东西不得行?我妈稀里糊涂挨了一顿巴掌。我爹预备再打,这时候就有拐棍儿敲在他头上。那是县卫生院的张鹤年张大夫,早年间和我爷两个,一把叉子下河抓鱼。张大夫是莫家故交,辈分又高,挨了他的打,我爹只得停手。他心里当然还是理直气壮,那条扔在地上的黄辣丁就是铁证。用科学的话来说,老爹申辩,这他娘的就叫做“基因”。
任凭我爹聒噪,张鹤年不作言语。老大夫年事虽高,双眼却是凌厉,蹲在水泥地上研究半晌,起身时手里已拎着那尾小鱼。他捻须而笑,说莫家祖坟冒青烟,此乃大吉之兆。经他指点,大家这才看见,鱼头上少了两枚鱼眼。说到这儿你们就要问了,鱼眼珠子能证明什么,怎么就成了吉兆?别说你们,就连莫家也不晓得其中门道。不过只要张鹤年张老爷子在,事情就好办。我爹当即沏了茶水,请老先生讲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山水江城,富饶之地也,粮丰廪实,因之素招匪患。匪寇每每绑票,必先探知家底厚薄,方可酌情开价,索要银钱。然本埠富绅,多治家有训,行走于市,皆衣着简朴,貌相不可知贫富。惟一法可行,名曰“试鱼”。莼鲈之思,人伦常情,江城食鱼,亦嗜如命也,不论贵贱,乡味难移。贼匪每猎人,必饿其三日,翌早,开斋派饭,止一尾鱼,一双箸。肉票吃鱼,匪自窥看,门道何在?单看头一著。凡人经此一遭,肚内必空,若糟贫之家,此刻但求饱腹,必先食肉厚脂腴之鱼脊,那匪见了,知其家徒四壁,便自放了去;若小康之家,虽饥肠辘辘,不屈肥甘厚味之享,必先食爽嫩弹牙之鱼腩,那匪见了,知其家境优渥,可大赚一笔;惟钟鸣鼎食之家,厄于口腹之欲,而不以荤腥乱心境,必取鳃下玉润凝脂之月牙肉食之——
这样说你们就明白了?张鹤年讲完掌故,问我爹道,吃哪儿不吃哪儿,命格使然,你们莫家出过几个吃月牙肉的?伯夷采薇,屈原餐露,陶潜饮菊,现在这个小王八蛋嘬鱼眼,比起莫家八辈祖宗,不知高道哪里去了。老先生留下一句后生可畏扬长而去,这下不光我爹,整个莫家就都放心了。我妈第一个反应过来,老爹的巴掌她都记着数呢,她把我换到左手,腾出一条胳膊,翻倍偿还了这一切。透过那上下翻飞的巴掌,我看见老爹笑面如花,那就是他在我人生中留下的第一帧肖像。
老莫说完,长叹一气,层层嵌套的故事终于回到塘边凉棚。光顾着听热闹,不知过去多久,太阳已没那么毒,倾斜的光线给鱼档老板整个人镀上一道金光。可能人过了三十就是这样,他解释说,脑子退化,陈谷子烂芝麻记得清清楚楚,眼跟前的事儿一晃倒模糊了。老爹死了七八年,他说,早没感觉了。
如蒙大赦。我和刘总相视一哂,钩上还是没什么动静,渔档老板的故事反倒钓起了我们的兴致。后来呢,刘总忍不住问,继续讲讲。他指着我说,这位是报社编辑,后头给你登报宣传,这生意不就起来了。人家没搭腔,任凭刘总满嘴跑火车,老莫自顾自接着说:
莫家规矩,儿子长大,定要继承家业的。自我两脚着地开始培养,先是喂鱼汤不喝奶水,这样养到旁人学走路的年纪,我就要下水。那时候我爹背着渔网,网里兜着一个我,我们爷儿俩下到云水河,等老爹踩好网点、下好地笼,我们就泡水里睡觉。这时候你需要穿一件长袖,一来防晒,二是提供浮力。先下水浸湿,起身扣紧腕口,再把下摆塞进裤腰,就可以下河了。找水流平缓处,仰面躺倒,胸腔留半口气,恰可露出一张脸呼吸。当然这是对一般人而言,像我爹,顶着一副硕大啤酒肚,浮力有富余,我就可以躺他大腿上,拿他肚皮当枕头。不多时,你不动弹了,麻叶儿小鱼就要上来咬,衔你卵蛋,偷吃脚底死皮。小鱼汇集,引来大白鹭,它们就站在老爹肚皮上,伸起长喙钓鱼。有时候来得多了,嫌我挤占它们的钓位,还拿爪子踢我脑袋。我受不了疼,就跟我爹告状。老爹嘘我一声,说难挨之处,正是修行时。莫家捕鱼不用强力,靠的就是修炼水性,亲近水族,跟这些鱼禽鸟兽搞好关系,方有愿者入网,以资果腹。再说这云水河上,捕鱼的也不止咱一家,鱼鹰、日鳽、大白鹭、斑鱼狗,它们吃了几百万年的鱼,算起来是咱抢了人家生计。我若有所思点点头,老爹继续说,不过一码归一码,欺负我儿子的事得另算。他把草帽从脸上摘下,瞅准时机盖在水鸟脑袋上,再把肚皮一缩,大白鹭反应不及,跌入水中,就成了落汤鸡。我连声叫好,那些大鸟也知老爹不好惹,纷纷扑棱翅膀,骂骂咧咧飞走了。
这么一阵折腾,觉也没了。日头渐弱,我爹便收了网,再把我捞起,和草帽、衣裤并排摊放在青石板上晾干。凉风贴着河床爬过,裹挟了水草的咸腥,鼻孔里钻进丝丝缕缕的柴火香气,那是我爹正在烧烤今天的渔获。我的屁股往往是他的计时器,两片屁股风干,烤鱼也就到了火候。父亲始终谨记张鹤年张大夫的教诲,他总是挑出当天最漂亮的一尾鱼,烤熟之后,剥下鱼眼,盯着我吞服。说到这儿,老莫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那时候我还真的挺爱吃鱼眼睛,他用了个比喻,滑溜溜就像果冻。那时候?出于一个编辑的职业敏感性,我似乎察觉到什么,意思是你现在不吃了吗?老莫点点头,不光是眼睛,凡是鱼腥我都不沾。这里头有蹊跷,我还想问,刘总打岔,你不吃我们吃啊。胖子易饿。要到饭点儿了,竿头又久久不上鱼,刘总心里开始发毛,你这塘子里到底有没有货,不会是骗我钓位费吧。渔档老板没理他,还记得莫家祖传手艺吗?老莫手指鱼塘,说,愿者上钩。我们眯起眼睛,这才发现他已提起鱼钩,距离水面足有二寸。开玩笑吧,你家也不姓姜啊?不容刘总置疑,老莫甩动鱼竿,与此同时,一条黑影跃出水面。老莫喊一声,抄网。“网”字落地,那不明物体已飞上岸来,刘总支起抄网,正中网兜。
本地翘嘴,属肉食鱼类,非活物不吃,鱼钩悬于水面,摆动如虫饵,反倒引其攻击。网兜里,大鱼吧唧嘴巴,像是在肯定鱼档老板的解释。老莫抠着腮壳把鱼拎起来,从头至尾,与他一条腿等长。足够你两人吃了,他对我们说,难得有人愿意听我念叨,帮忙钓鱼的费用就免了,按斤两付餐费就行。
老莫说完就拎着鱼上后厨,我跟刘总倒有点摸不着头脑。这又是玩的哪一出?我问刘总,刘总摇摇头,不知道,论坛里也没见有人说,可能是聊得比较投机?得了吧,我说你聊啥了,全程都是他在说,真假还不一定。管他呢,刘总心宽,有鱼吃就行。翘嘴可是好东西,他指给我看,老莫正在水池旁宰鱼,大鱼离水,对陆上世界充满好奇,正抬眼看世界,刀就进来了。老莫手上有准头,刃口劈开阳光,如鱼鳍划水,一刀正中脊椎,深三寸,劈下半个鱼脑袋,余下身体还在扭动,截面处可见白嫩嫩的肉。老莫继续科普:翘嘴生性凶猛,却头脑简单,一刀断了神经,反应不过来,因而没有痛苦。只有死时舒坦,才能保证肉质鲜美。鱼档老板瞧着年轻,手脚竟很是麻利,清理完翘嘴鱼,又拱手说句“君子远庖厨”,便上料理间去了。有这么玄乎?我问刘总。这事儿怎么说呢,上回吃德国大肘子,主厨还说他们家的曼加利察猪宰杀之前要听贝多芬呢。口味有没有区别不知道,不过这莫家倒真是养鱼大户,刘总说,我跟做餐饮的朋友打听过,十年前,全江城活鱼馆子里的货,都是从莫家塘里捞上来的。那时候他家生意做得大,从精品鲍参翅到平价鲢鳙,种类齐全,品质也高。可不知什么时候起,莫家的鱼就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老爹挣够了钱不愿再碰鱼腥,也有人说贩了不该贩的东西,让工商局给吊销执照,总之莫家老爷子没有好命,死在正当享福的年纪,到底怎么回事,刘总拿下巴颏指指门口,可能只有他知道了。刘总刚说完,老莫已经端着盘子进来了。这小子还真有点功夫,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相信这满桌子的菜是拿一条鱼做出来的:剁椒鱼头、水煮鱼片、红烧鱼排、泡椒鱼肚、香酥鱼鳞、凉拌鱼皮。翘嘴鱼死得其所,从头到尾一点不浪费。刘总把车上的酱香也拎了过来,他满斟三杯,一杯留给自己,两杯让给老莫,最后冲我赔个笑脸,说辛苦一下,回程开车。我倒无所谓,对酱香没什么兴趣,只是老莫也摆摆手。刘总想起来了,莫老板餐露饮菊,当然不会碰这浑浊之物。便用公筷戳下剁椒鱼头上那对大眼泡子,刚要端过去,那老莫依旧摇头:我说过,早就不吃鱼眼了。于是我问出之前那个没有说出口的问题:什么时候?
当我知道那是一双眼睛的时候。
老莫看着我说:在我吞服鱼眼的第十七的年头,高考成绩单彻底断绝了我成为天才的可能。虽然我爹依然对张鹤年的预言深信不疑,但他已经很难找到一副合格的鱼眼供我吞食。云水河搞梯级开发,竖起一座座拦水坝,江城段径流量逐年减少,老爹的渔获每况愈下,即便捕到些歪瓜裂枣,也都是瞎鱼。它们眼泡干瘪,眼窝深陷,巩膜当中只有又咸又腥一汪苦水。终有一日,用如今钓鱼佬的行话来说,我爹走了“空军”。
那是一个燥热的夏日黄昏,老爹拖着两匹网到家的时候《新闻联播》都放完了,不知道那天他抛了多少回网,两臂早已力竭,摁遥控器的劲儿都没了。我妈端来汤饭,我帮他打开电视,他头都没抬一下。多年以后翻看族谱我才知道,自明嘉靖三十二年至今,凡四百六十余年,莫家未尝“空军”。老爹这一回,也算是在家族历史上首开纪录,他担不起这罪名,看完《天气预报》就有了决定。莫家不擅夜捕,老爹执意独去。他喝了两碗紫菜汤,恢复些体力,又拎两瓶啤酒放在网兜里,然后独自一人走向云水河。那一夜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第二天一早,公安局打来电话,说他们的兄弟单位,雒城刑侦大队找到了莫栋国。雒城在云水河下游,距离本县三十公里,公安说人没事,漂在采砂坑里睡着了,目击者当成浮尸报的案,打捞组下到现场的时候他还在打呼噜。那鱼呢?我直接问重点。什么鱼?人家没听明白,说我们把莫栋国拽上岸的时候,他怀里只有两个空啤酒瓶,和一件金色连衣裙。
人既然没事,我妈也就没有追问细节,只是莫家千百年传承的捕鱼古法就此被宣判死刑。在我妈的主持下,莫家转型进入渔货批发市场,老莫渔档正式开张。我妈进货,我爹在鱼档杀鱼,那个暑假我给他打下手,开肠、破肚、刮鳞、扒鳃之后,留给我一道挖鱼眼的工序。外省贩来的也都是瞎眼鱼,腐黑的两坨烂肉实在不成卖相。我从小吃这玩意儿,厌恶比旁人更甚。一天活儿下来,我恍惚看到水磨石地面坑洞密布,细看才发现,那是密密匝匝的鱼眼睛。它们又干又瘪,每一颗就是一个摇晃的漩涡,从中放射某种磁力线,令我晕眩不止。我感到手中的鱼刀沉重而迟钝,鱼档突然变得腥臭难耐,那天晚上,某种潜藏已久的厌恶变得具象,我恶狠狠地冲着他们两个说,我要上大学。随即将一腔胃液倾吐在鱼案上。张鹤年张大夫也是个老糊涂,他再怎么神通广大,也不懂得密集恐惧症这回事。草药接二连三灌下去,我这见着鱼腥就犯晕的毛病却总不见好。继承祖业无望,老爹如丧考妣。那时候张大夫就跟他说,多读书也好,知识改变命运嘛。
从小到大吞服的鱼眼珠子没能换来试卷纸上的漂亮分数,但冥冥之中似有莫家先辈惦念,惦念着莫家祖业。我们全家拿着本省专科院校招生简章研究了三天,综合录取成绩、离家距离、学费因素,最后我能报的就剩一个,渔业资源。后面的事情显得乏善可陈,老莫说,年轻时候都想往远了跑,躺在大学宿舍玩手机的时候,还操心人类什么时候上火星。他端起桌上苦荞茶一饮而尽,接着说,兜兜转转一大圈,还是回到了老爹留给我的鱼塘。以前家家户户都买大鱼,蒸大肉,吃个肚腹饱满,现在大鱼大肉没人稀罕,反倒是些杂粮野菜流行起来,江城吃鱼的时尚,也从吃饱吃好变成了吃味吃鲜,讲究绿色有机,野生自然。这就算是撞上了,我爹放养的这几塘小鱼,因此卖得个好价。
鱼档老板这么一说,真像那么回事。一桌全鱼宴已被我们吃得差不多,细细品来,鱼头爽嫩,鱼腹紧实,鱼皮弹牙,确是酒楼饭店菜市场里那些养殖鱼不能比的。那老莫得意起来,珍惜吧,他再次强调,出完这塘货,就再吃不着了。刘总不明白了,从生意人的角度来说,如此赚钱的买卖,只有做大做强的道理,哪有自己盼着关门歇业的?想不通就对了,老莫冷冷说道,因为我爹死在鱼上头。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贩鱼以来,多少年没下过河了,那天非要撒网捕鱼。寒冬腊月里,不感冒才怪,进医院的时候已经转成肺炎。几十年的旱烟卷烟水烟早就把他的肺糟蹋得不成样子,一来二去,肺炎变成气肿,气肿又成积水。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我妈已经伏在床头哭得眼窝深陷。病床上,同样干瘪的父亲眉目紧闭,仅嘴角还有一丝攒动。我握着他的手,感到温暖而柔软,不知他是否也觉察到我的到来。房间里只有呼吸机旋转发出窸窣声响,我妈缓过劲儿来,说住进来半个多月,张鹤年的草药汁子也灌了几大桶,到底没有起色。也就是今天你回来,脸色活泛了些。老爹像是听到我们的谈话,尝试着冲我点头,只是鼻腔里呼吸管插得深,发出的声音词不成句。我凑近听了听,然后告诉我妈,这里有我,老爹让她回家歇着。等我妈走了,我又回头告诉我爹,说妈已经走了。“走”字刚出口,还没有加上完成时,老爹的眼睛就亮了起来。我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于是看见我的父亲,肺炎病人莫栋国,这个小老头子一把扯掉呼吸管,抖擞腿脚站了起来。
卫生院侧门出来,就是云水河堤,小时候跟父亲下河捕鱼的时候还是煤渣路,如今已整饬一新,变成滨河公园。花木掩映之下,一条鹅卵石小径向上游延伸,父亲于是把拖鞋提在手里,赤脚着地,他说这是张鹤年传授的延寿之法,张鹤年教了他不少东西,包括如何装恙骗过我妈和护士。我说你骗我妈干啥。他叹了口气:小莫啊小莫,这事本不愿讲。病过这一遭才想通透,虽已不事渔猎,你到底是莫家的种啊。莫家的秘密怎能不告诉你呢?趁这会儿精神头,我干脆给你讲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小子爱听也罢,不耐烦也好,这就是我这个当爹的,能留给你最后的东西了。
父亲拽着我的手,拣条石凳坐下。还是你爹我没本事啊,他像一个老友那样跟我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何况你那专科学费动辄成千上万呢?可你要是以为我三四十年来每日下河,单就是摸两条小鱼儿,那可是小看你爹了。还记得你中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吗?就是我被水冲到雒城那回。我点点头,时过境迁,那件事早已模糊,或者说不再重要,唯独我妈始终对老爹怀里那条金丝罗裙揪住不放。当时在雒城江边,救人要紧,来的警察又都是大老爷们儿,只当那裙子是漂浮垃圾,没人瞧出其中门道。只有我妈留了个心眼,他把衣服裹在毛巾里带回江城,当晚就发现问题,用她的话说,且不论这罗裙用料之讲究、阵脚之细密,单这腰身尺寸,就不是一般女人穿得了的。还有什么能比发现男人偷情罪证更能让一个女人兴奋呢?她开始研究这件裙子的每一处针脚,每一道纹饰——
可是你妈哪里懂,父亲接过我的话头继续说,什么龙鳞纹蛇鳞纹,那罗裙上绣着的根本就是鱼鳞纹。你要问为什么?那是抱在我怀里的,我能不知道?我告诉你吧小莫,那裙上绣着的既不是鲫鱼鳞,也不是鲢鳙鳞,那根本就是鲤鱼鳞。云水河里有金鲤鱼的事情,只有我莫家知道。老爹转过身来,时间仿佛回到多年前我们寻找他的那个夜晚:那一夜,我在河里泡了整宿,你以为我在干吗?我没有暖炕席也不是蹭痒痒,你明白了?那金鲤鱼一窜进我的怀里,立马化了人形,那腰身,那屁股蛋子,你们以为你妈能比?你爹是有家伙事儿的人,我说的不是酱萝卜也不是擀面杖,你明白了?不怕你笑话,我三十岁才找的你妈,我就是等着这位鲤鱼姑娘。那会儿还没你呢,鲤鱼姑娘的鲤鱼老爹就许了这门亲。那条金丝罗裙,就是鲤鱼姑娘留给我的信物。可谁又能想到,任凭我这手艺如何精进,也赶不上世道变化啊。你看那云水河,一夜之间筑起坝,蓄足水。大河上下,变了模样,我的鲤鱼姑娘怎么找得着我啊……
好你个老莫,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一句响亮的声音打断了父亲的故事。放眼河堤,并无旁人。水面上风平浪静,我扒着栏杆张望,只看见离岸不远处,一串气泡翻腾不止。不用找了,那声音接着说,我就是你们说的鲤鱼姑娘。我循声望去,刚才冒泡的地方已经绽开簇簇细浪,浪尖果真托着一尾鲤鱼姑娘。跟动画片里拖条大尾巴不同,她已完全幻化人形,只有下巴上保留的两条鳃裂显示她曾是一条鱼。想必她在水下监听已久,我爹指不定扯了什么谎,吹了什么牛。鲤鱼姑娘实在听不下去,朝岸沿儿上啐了一口河水。她说:二十年前那个元宵夜,我贪玩赏灯,误入莫家罗网,是你将我放生,我因此老早就相中你。不想大河之上筑坝蓄水,改换模样,苦了我寻你整二十年。挨千刀的莫栋国,你知道我是真心的,花哨日子我不去想,可衣食住行总得妥帖。上次见面说的话还记得吧,爹爹说我们做鱼的离不开水,虽炼成人形,也不能离河太远,非得在这河堤上寻处僻静院子才好。不知道这事你办好没有?
问题悬在那里,我的父亲无处可逃。鲤鱼姑娘像是有点生气,腮帮子鼓囊囊的,翕动不止。鱼类没有眼皮,两只眼睛因此更显巨大,老爹只跟她对了一眼儿就都老实交代了。
办个逑。他说,河边的房子买不起啊。要说这大河两岸早先全是烂泥塘,我拉屎都不来的破地方,咱爹要是早些年给我捎话,甭说一处宅子,我随便撒泡尿留个记号,那整片地不都姓莫了?今时不同往日,高楼大厦平地起,就成了什么“江景雅居”“滨河花园”“丽水别墅”,就靠我这打鱼的手艺,拼上老命买块地皮,别说住了,包饺子皮都不够啊我的鲤鱼姑娘,鲤鱼姑娘……
任凭父亲如何呼唤,鲤鱼姑娘恢复鱼形,尾巴一甩,那抹金色便往河水深处遁去。我爹大叫一声,从石凳上一跃而起,等我回头时他已腾空,我伸手要拦,却只抓住他一只裤脚,我不知道老爹哪里来的力气,他几乎是拿出所剩无几的全部生命力,拽着我一道飞过护栏,此生最后一次进入云水河。
随着故事结束,老莫端起早先斟上的两杯酒,逐一饮净,感觉不解渴,又把壶里苦荞茶喝干,才长舒了一口气。肴核既净,我看一眼手机,竟然都十点多了。刘总怅然,不知是吃太多撑的,还是因为酒桌上的故事。渔档老板送我们来到院子里,刘总拍拍他肩膀,说老爷子撑桨逐浪一辈子,魂归云水河,也算死得其所。老莫打断他,我爹到这儿还没死。刘总不明白了,你不说因为一条鱼死的,鲤鱼姑娘呗?不是这条,老莫说,等我醒来的时候父亲已经回到卫生院的病床上,床单被我的口水濡湿一大片。他发梢未干,尚在滴水,耳垂上还缠着几丝水绵。后来我又追问过几回金色鲤鱼,老爷子笑呵呵,完全不记得说过这回事。不过他的精神倒是一天天好起来,没多久就出院了。我记得回家那天,父亲心情大好,非要自己下厨,感谢妻子二人伺候病榻。他还特意上菜市场买了一条罗非鱼,说是这东西最近流行,下一步咱莫家也要拓展新品种。他边拾掇鱼边和我们说话,就是这么一分心,大拇指让鱼鳍扎了一下。当时不会有人想到,打了一辈子鱼的莫栋国,会因为一条罗非鱼丢掉性命。可是仅仅过了两天,我爹的右手已经肿得似个猪蹄。这是报应吗?父亲在弥留之际追问张鹤年张大夫。后者摇摇头:是不是报应不知道,我只知道细菌感染并发败血症,神仙来了也没办法。
晚风涌入院子,带来淡淡草腥。我和刘总学老实了,不知道后头还有没有下文,都不敢接话,直到老莫递过来餐费账单,才确定这回真的是大结局。刘总扫完付款码,问渔档老板怎么回家,要不要我们捎一段儿。我就住这儿,他说,不少钓鱼佬喜欢夜钓,我得防着点。那不刚好,刘总说,早点处理完你就解脱了。那也不能当冤大头啊,十几万块钱呢。果然做生意的没一个吃亏的,刘总问,你的故事都讲完了吗?老莫狡黠一笑,等你们啥时候再来钓鱼就知道了。下回凭自己本事吃鱼吧,我不会给你们帮忙了。不等说完,老莫已经转身,他远远地冲我们摆了摆手,消失在墙角尽头。
还真是个奸商,刘总刚摇上车窗就把笑脸收起来,他坐在副驾跟我抱怨,说一条鱼收了两千多。什么意思?我说下次我请行了吧,再说两千块不光吃鱼,你还听场故事呢,不亏。可是谁知道故事是真是假?刘总反问。我说信则有呗。随口一说,没想到刘总点点头觉得有道理。我说你还真信啊,刘总把手机晃了晃,我专心看路,他就念给我听:云水河江城段虽不是什么名川大河,却见于诸多典籍,据本市学者考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里的“河”,指的就是云水河,李太白曾泛舟于此掬水中月,辛弃疾“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更是直接描写了江城元宵夜之盛况,而词中所谓“鱼龙”,即云水河特产金鲤鱼……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懒得听网络上的胡扯,牵强附会嘛。刘总说这可不是小道消息,正儿八经文旅委官网上的帖子,关键是作者,你猜是谁?我拿余光瞥了一眼,只见刘总两颗眼珠子闪闪发光,夜猫子似的。署名张鹤年,刘总对我说,江城民俗文化协会名誉会长。
话音甫落,我一脚急刹,刘总手机脱手,像一颗炮弹砸向挡风玻璃,身后的扬尘随即将我们淹没。刘总骂我会不会开车,我根本说不出话,剧烈的咳嗽几乎将我整个人由内而外撕碎。刘总摁开车顶灯才发现事态严重,等他把我从车上拖下来,我感觉一条命已丢了七成,恍惚中只听见刘总埋怨我口不择言,肯定是触怒了河神水怪鲤鱼姑娘什么的,他的声音变得柔软,被河风一吹,就飘到机耕路两侧芦苇荡里去了,我朝着刘总消失方向,竭力聚焦目光,看见一条肥硕的金色鲤鱼正在游荡。萤火虫在它身后整齐列队,夜空因此变得斑斓,就在我高高跃起,伸手想要抓住那条尾巴的时候,刘总把我拽了下来。
科技改变生活啊,幸亏我手机信号好,他说,海姆立克急救法,跟着小视频现学的。
有惊无险。我一口气喝完了刘总递过来的矿泉水,没告诉他刚才看见了什么。我打开手机电筒,蹲在机耕路上找了半天,从沙土里把那枚鱼骨揪了出来。就是这个?刘总接过鱼骨,放在SUV的远光灯前细细端详:翘嘴身上有这个形状的骨头?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还想问它怎么卡我喉咙里的呢。我跟刘总说,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得谢你。嗐,瞎猫撞见死耗子,刘总耸耸肩膀说,再来一回,我还不一定敢上手——不为这个,我打断刘总。他愣了愣,没反应过来,这时候我就笑起来:干了十几年编辑,从未如此深刻地理解过一个成语,我告诉刘总,这他妈的就是“如鲠在喉”的滋味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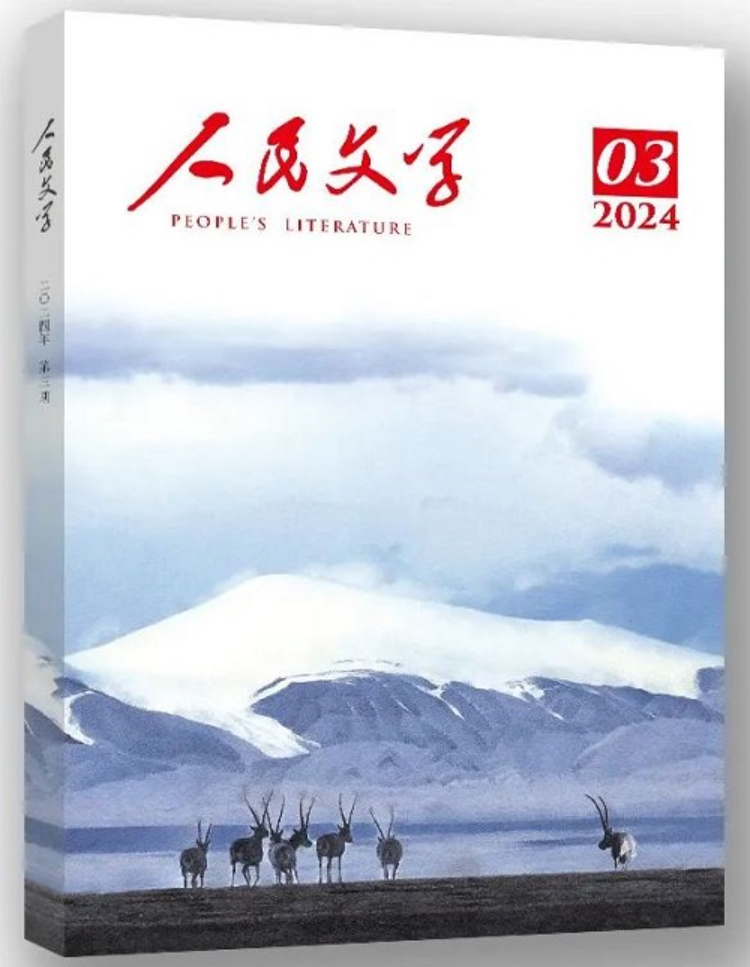
(原文刊发于《人民文学》2024年第3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