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丨蔡晓安:向钥匙 推荐丨蔡晓安:向钥匙

向钥匙
文/蔡晓安
在新县城,在开锁这一行,向钥匙算是个另类的存在。其他开锁匠都是男的,即便是夫妻店,两口子都会开锁,也一定是男的在外打主力,女的是在男人有其它事情实在脱不开身的情况下,才帮忙打个替补。向钥匙不是,向钥匙虽然是女人,却是实打实的主力。说主力还不准确,如果把开锁当作演戏,她就是戏台上的那个独角。一台戏下来,从头至尾,都是她一个人“蹬蹬蹬”地挥汗如雨。
情况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向钥匙也曾经有男人。男人也是个开锁匠。男人不但是开锁匠,而且是新县城一等一的开锁匠。无论什么样的锁,小到各种五花八门的家用锁,大到银行的保险柜,只要他出马,没有打不开的。旁人看起来也没有多复杂,就见他东戳一下,西扭一下,正看得起劲呢,一个没注意,只听“咔嚓”一声,锁就开了。整个过程,既轻松,又自在。男人开锁不像在工作,更像是享受。享受锁被打开那一刻的愉悦,就像当初他打开媳妇那把锁时的感觉,也享受旁人钦服的目光。一个开锁匠,普普通通,平平常常,要被这样的目光所关注,唯独就在锁被打开那一刻。
锁在男人的手里,就像只扑来腾去的小麻雀,想飞飞不起,想逃逃不掉。他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然而,男人开锁技艺虽高,福命却浅。那一年,城郊复兴一个妇女打来电话,说锅里正炖着汤呢,不过是出门扔了一袋垃圾,人刚转过身,到了门口,不想一阵风来,竟把门关死了。妇人在电话里急得像马上要跳楼了。“师傅,师傅,麻烦你快点来!我灶上的火开得大。要是来晚了,我,我……”说着说着,一个没忍住,“哇”的一声就嚎啕起来。
男人骑着摩托,风驰电掣般向妇人家里狂奔。
很不幸,就在男人即将到达的时候,据说当时男人所在的位置,都能看见妇女家住的那幢楼房了,一辆大货车突然一个拐弯,迎面冲撞过来。男人的摩托就像只可怜的小鹿,一下子就扑进了老虎的血盆大口。事后的调查结果表明,大货车司机当时正一边开足马力,一边接听电话。想的是,反正是笔直大道,视野又好,没关系。哪知正要与男人骑的摩托会车时,左前轮突然爆裂,车身一偏,就向摩托车对撞过去。男人也快,急着要去开锁,也是开足了马力。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整起事件中,稍令人欣慰的是,那个妇女左等右等,没有等到师傅去开锁,又连续打了他好几个电话,也不回,只好在墙上的“牛皮藓”中另找了个号码。门终于打开,进厨房一看,竟然屁事没有。原来,妇女被关在门外时,锅里的汤才放到灶台上。刚开始炖,火开得大。因为火大,水又加得满,“叽叽咕咕”一开,大个二个的水泡挤到锅边,争先恐后往外窜。水泡一出锅就破了,破了的水泡变成了水,沿着锅壁往下渗,几渗几不渗,就把锅底的火渗灭了。
男人走了,但男人的名号还在。
男人的名号叫向钥匙。所以严格来说,向钥匙不是现在的向钥匙,而是现在向钥匙以前的男人。
向钥匙的男人被车撞死了,向钥匙就成了寡妇。好在他们的儿子已经在读初中,除了保证他的吃穿住用等开销,不再需要额外的照顾。向钥匙本来打算将男人死后得到的那笔赔偿金用来开个小店,但思前想后,还是觉得,要把那笔钱存起来。孩子才十四岁,花钱的日子还在后头。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万一开店赔了,到了孩子需要花钱的时候,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那就索性继续干开锁这一行吧。
男人还在的时候,没少教过她。男人教他的目的跟其他夫妻店差不多,一个人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把老婆教会了,多少能打些帮手。男人技艺高,女人脑子也灵性,一个教得好,一个学得快。如果男人不过世,他们在开锁匠的世界里,说是“山伯配英台”,同行们也不会觉得有多过。
但那毕竟是男人还在的时候。现在男人没了,向钥匙就觉得,有男人的世界,与没男人的世界,真正有天壤之别。比如,男人在的时候,无论多么晚,哪怕是半夜,只要有人打电话来求开锁,他一定二话不说,下了楼,骑上摩托就走。大多数开锁师傅,在这个时间点,要么手机不开机,要么手机开着不接听,要么接听了直接说睡下了不出门,反正没几个愿意半夜三更还往外跑的。向钥匙当初也不愿意男人太晚了还出门。夏天还好,特别是冬天,两个人在铺盖窝里搂着,暖暖和和的,多好。人一走,等他回来再蜷进被窝,把觉耽搁了不说,好半天都冰凉凉的。但男人不同。男人说,你不去,人家就只能在外面呆一晚上。现在让你去外面,看能不能呆上一晚?
虽然不是十分乐意,但男人的善良终归感染了她。她想,有这样一个男人,虽然钱没多少钱,旁人嘴里眼红眼热的权势更是谈不上,但与他相守一生,能让人心安,也是一种好。
所以,当她现在独自面对的时候,碰到半夜打电话来的,虽然也知道一个女人这个时候出门,实在不妥当,但咬咬牙,把心一横,还是出去了。
那天出门,她特意看了看手机,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好在是大热天,到了街上,一丝风过,头脑就清醒了大半,那种感觉,反倒比呆在屋里好多了。
到了电话里指定的地点一看,只有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在。向钥匙也见怪不怪。云阳是江边小城,很多人喜欢在这样的夜晚约三五好友,聚在“好吃佬街”边喝酒边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后半夜。碰到一些邋遢的,酒儿喝饱了,肚皮填圆了,回家一摸钥匙,立马就傻了眼。一些是因为老婆故意在屋里装着睡死了,无论男人在外面把门砸得地动山摇,也丝毫听不见;一些是屋里根本就没人,要么这关在外面的人本来就是个单身汉,要么不是单身汉,也刚好碰到这天,家里其他人都不在。反正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也恰是有了这各种各样的情况,电话才会打到她向钥匙这儿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邋遢的主儿,可是她的衣食父母呢。所以,虽是半夜了,内心里的报怨是不应该有的。不但不能报怨,还应该感激。
没有他们,她靠什么吃饭呢?
向钥匙开锁的时候,男人一直在身后喘着粗气。像很多年前农村用的那种土灶,“噗呲噗呲”拉风箱的声音。不同的是,男人拉的“风箱”不仅刺耳,还夹杂着难闻的酒气,每打一次嗝出来,都伴随着十分浓重的酸臭味。向钥匙强忍着,尽量使手里的动作更快点。刚才上楼来,她不由自主地瞥了他一眼,只觉肉敦敦的样子,仿佛浑身上下都堆满了肥肉,皮带一松,整个人都会垮掉似的。圆滚滚的脸上,即便在昏暗的楼道里,也依然像挂了漫天的彩霞。
向钥匙心想,何必呢?酒跟人又没有仇,非要跟它较高低。
门很快就开了。向钥匙说:“大哥,八十。”
开锁一次,收费八十元,这在新县城是大行大市的价格。
男人嘟囔着,语词含混不清地说:“八十啊?这么贵!我一天累死累活,都挣不到这个数呢。你倒好,比我撒泡尿的时间都短,钱就到手了。”边说,就见他边把手往裤兜里伸。摸了半天,取出来,手还是那只手,光麻麻的,什么都没有。但那一番捣腾的动作,也不知是不是因为碰得了敏感部位,却让男人的呼吸变得更加粗重了,活像一头正被追赶、马上就要送上案板的猪。
向钥匙心里“咯噔”一声,但她还是机敏地提醒道:“大哥,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用现金!用微信嘛。”她的声音有点大,目的是想转移男人的注意力。
男人一听,眼睛像突然被拨亮的油灯,神色也变了,讪讪的,诡谲而迷离。男人像换了一张脸,嘻笑着说:“对对对!微信微信!加了微信,我们就是朋友了。朋友,钱算个什么呀?我微信上有的是钱!别说八十,再翻个倍,也行啊。”
他猛地上前一步,笨重的身体像一座山,直压过来。“八十,再翻倍。说好了,就这样哈。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向钥匙大惊失色。她急切地央求道:“大哥。你喝多了。钱,我不收你的了。你让我走吧!”她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却不知,人已经从门口退进了屋里。
男人的喘息声越来越重,越来越粗。他的眼里泛着灼热的光,仿佛把整张脸都要燃烧起来。
向钥匙正准备大声呼救,一团黑影像从天而降的天兵,一下闪到男人身后,只一把,就将这团胖乎乎的肉球推了个狗吃屎。然后,一步跨到她身边,拉起就飞奔下楼。
向钥匙怎么也不会想到,凌晨英雄救美,将她一把从虎口拖拽出来的人,竟然是郝新。说起来,这个郝新也不是外人。那还是她男人在世时候的事。干开锁这一行的师傅,为了手头更灵便些,往往都会收徒弟。一方面徒弟会给拜师钱,另一方面,碰到开锁业务太繁忙的时候,徒弟又会打些帮手,还不用专门给徒弟开工钱,也算节省了一笔,可谓一举两得。但开锁是特殊行业,不是什么人说干就能干的。如果是拉起杆子,要正儿八经开门营业的师傅,必须先到公安局,又是抽血又是验指纹,一趟下来,什么问题没有,才算过了第一关,然后才能去工商局办营业执照。如果是师傅要收徒,也必须领着徒弟去公安局,也是一样抽血验指纹。不同的是,如果是师傅,要把各项查验结果录入到专门的系统里去,徒弟呢,录入系统这一环倒是免去了,主要是跟系统里的数据比对一下,看有没有前科。没有前科,才算有了学这一行的最基本资格。有些师傅怕麻烦,收徒不愿往公安局跑。不出事倒也没什么,公安局也不会三天两头派人来查,但倘若哪一天你收的徒弟在外面惹了事,不打招呼就把别人家的锁开了,堂儿皇之地在别人家里如入无人之境,只要被抓到,那么师父也会跟着一起吃不了兜着走。如果时间再往前推十来年,那时候要入这一行,还必须到公安局拿“特种行业许可证”才行呢。一句话,对开锁师傅来说,打开一把锁是很容易的事,可要把开锁这一行的“锁“打开,却不是说起来这么简单。所以偌大个新县城,常住人口近四十万,把开锁当饭吃的,不过二十多家,而真正精通的,顶多也就那么十来家。曾经的向钥匙,也就是现在向钥匙的男人,可以算这十来人中间最为拔尖的那几个之一。
这么厉害的开锁匠,收个徒,也不是手到擒来的事。纵然你的水平再高,本事再大,可真正想往这一行钻、在这一行里求生存的年轻人,却总是寥寥无几。有些人即便学会了,被收入更高的职业一吸引,又头也不回地做其它去了。
向钥匙的男人曾经先后收过几个徒弟,只是后来继续留在开锁这一行的,一个都没有。郝新是他收的几个徒弟中脑子最灵活的一个。那时候,他刚初中毕业。高中没考上,出去打工,除了搬砖,什么都不会。可就算搬砖,他跟其他人一比,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其他那些搬砖的,不是五大三粗,就是腰圆体壮,就算瘦,也瘦得有肌肉。他的瘦,却是真瘦,瘦得跟只猴子似的,仿佛把包在外面的那层皮一剥,露出来的,就是那副可怜兮兮的骨架了。
后来还是他父亲拿的主意。父亲说:“去年我们家房门打不开,请了个开锁匠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打开了。一眨眼工夫,几十块钱轻轻松松就到手了。我看啦,依你这德性,别的肯定干不了,只能干这个了。”
郝新跟着向钥匙的男人学了开锁技术,却终归不愿在新县城这个小地方蹦跶。一个哥们儿一声吆喝,就跟着跑到广东闯大世界去了。
跑到广东都好几年的郝新,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向钥匙开锁的那家人门口呢?而且还是在大半夜?向钥匙十分疑惑。郝新说:“娘师,说来也是凑巧。我在广东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坐了长途大巴回来。不想客车在路上出了故障,耽搁了。到新县城的时候,都快夜里一点了。我就想,反正家离车站也不是很远,身上也没几个钱了,打车终究有些心疼,不如走回去。哪知到了半路,正好从师娘家楼底下经过。就见师娘发动摩托,急忙忙地冲出去。我喊了两声,您没听见。我觉得很奇怪。这么晚出去,肯定又是去帮人开锁,但怎么不是师父,却是师娘呢?师父就不担心,您一个女人家,万一出点什么意外,可怎么是好?我也来不及细想,赶紧拦了辆出租车。我是想,不管师父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出门,反正我是他徒弟,不能让师娘一个人在外面,让师父担惊受怕。”向钥匙心里的疑虑并没有完全消除,又问道:“可是,你跟上来,为什么我没有发现呢?”郝新有点不好意思,一边搓手,一边低下头,说:“这个嘛,一是因为您跑得实在太快了,不要命似的。我知道肯定是那边催得急。另外,我也不想让您发现后面有人跟着。这么晚了,您又不知道跟来的人到底是谁。万一想多了,受到惊吓,您跑得那么快,反倒更危险。”
郝新这样一解释,向钥匙在脑子里又回味了一遍,好像也是那么回事。向钥匙说:“你不知道你师父的事?”郝新瞪大了一双黑溜溜的眼珠子,说:“不知道啊,前几年我都在广东,实在混不下去才想到回来。师父,他怎么啦?”
向钥匙就将男人的遭遇讲给他听。末了,一声叹息:“人各有命。是命,怎么躲都躲不过。”事情反正都过去了这么久,再说起,她心里就跟没有一丝风的江面似的。她知道,对于她这样的人来说,要想生活能够继续,就只有抬起头来朝前走。
生活,不相信怨天尤人。
生活,更不相信所谓女人的眼泪。
第二天,向钥匙起得很晚。因为头天夜里出去开锁,本来就耽搁了瞌睡,加上又遭遇了那样的突然袭击,一直惊魂未定。等她起床来一看,都中午一点多了。迷迷糊糊中,好像刚觉得可以放松下来,沉沉地进入梦乡,又突然一个激灵,像被警棍电了一下,又像被蜈蚣啊马蜂啊什么东西蜇了,总之是,睡,睡不深,醒,醒不全。半睡半醒之间,十来个小时就过去了。
向钥匙起了床,也不想做饭,就那么呆呆地坐着。不知不觉间,男人去世后,这些年的委屈和不易,像潮水一样就涌了出来,漫过颈项,漫过鼻孔,漫过眼睛,直漫上头顶……
仿佛再过那么一秒,她就可以和那些委屈和不易彻底说再见。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她这些年总是经历着那一晚那样的极端遭遇,更多时候,都是些小小的难受,小小的不平,小小的辛酸。但所有这些难爱、不平和辛酸汇积到一起,也就成了一条恣肆的大江,可以一泄千里,可以溃堤而去。比如,你明明接到电话,叫你去城郊人和镇上开锁,等你好不容易风急火燎赶过去,再打电话联系,却死活打不通。也不可能一直等在那里啊,开锁这一行,虽不是特别繁忙,业务总还是不缺。于是,只好又灰头土脸地往回赶。等你刚回县城,电话又来了。人家还理直气壮地质问,怎么这么久还不来?你们这生意还做不做了?你一解释,对方才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我搞忘了,我设置了“拒接陌生电话”。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再比如,磐石一个人叫去开锁,你到了那里,反复跟对方确认,你在电话里说的是四幢五楼一号,这里是五幢哦。不想对方把眼皮一翻,没好气地说,我自己家,还能搞错了?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你只管开锁,马上!结果等你把锁打开,门一推,刚才还没好气的妇女也没气了,屋里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突然看到房门无缘无故开了,门口还站着两个陌生人,显然受到惊吓,“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这个时候,你还不能转身就走。你还必须耐着性子跟房屋主人解释,这还不够,你还必须马上拨打“110”。只有警察到了场,证明你是开锁匠,确实是因为顾主交代不清把门开错了,才能彻底洗清你身上的嫌疑。
想起这些,向钥匙就觉得头又开始疼起来。她起身去了厨房,泡了包感冒颗粒喝下去,然后才慢条斯里地往楼下走。门市就在一楼,租的,很小,旮旯角落全算在内,也不会超过二十个平方米,但它毕竟是支撑她和儿子正常生活的唯一场所。其实,对于开锁匠来说,她这条件已算十分优渥了。其他大多数同行,都没有专门的门市,无非就是在街边摆个地摊,有人打来电话就去开锁,没有呢,就干些配钥匙、甚至擦鞋补鞋的活儿。想想也是,尽管新县城几十万人,但也不可能家家户户每天都把自己关在了家门外。真正有开锁需求的,总是少数。人长着一双手,就是用来刨饭吃的,不可能让它闲下来。一闲,就很难有活路。向钥匙的男人刚入这一行,连个地摊都没有,纯粹就是在全城(包括城郊)各个楼道里贴张小纸片,上面只有两个字:开锁,紧跟着就是一串阿拉伯数字,那是用来联系的手机号码。说白了,他在墙上贴的,就是我们俗称的“牛皮藓”,他那时候干的,就是开锁行的“游击战”。后来终于有了自己的地摊。再后来,男人说:“还是找个门市吧。不忙的时候,你可以守在门市上,兼卖些锁。”这时候,什么电子锁啊,密码锁啊,各种花样百出的锁都已经应运而生。现在想想,向钥匙还是挺佩服自家男人的。他虽然是个小开锁匠,却也懂得与时俱进。老抱着开锁这一个事不放,哪能把生活过得更好呢。
门市一打开,她就觉得身后上来个人。转身一看,果然是郝新。
郝新还是那副很腼腆的样子,进来就说:“师娘,我想求你个事。”声音有点小,像屎蚊子一样嗡嗡嗡,不仔细听,都不知道他到底说的什么。
向钥匙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千万别说‘求’。”
“我在外面也跑了这么久,却始终混不出个名堂。我就想,还是回来当个开锁匠吧,更现实些。我本来是打算来求师父的,却不想……”边说,边哽咽了一下,继续往下说,“在外面跑的这些年,我把当初学的开锁门道全荒废了。我的意思是——”他有些欲言又止,头微微低垂着,怯怯地向她这边瞟了一眼,“师父不在了,我想跟师娘继续学。”生怕她不同意,又赶紧追加几句:“工资我不要。学徒费另给。等到我学会了,如果师娘不赶我走,我也可以留下来给您当帮工。”
郝新的这个要求,如果早一天提出来,向钥匙肯定会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她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说年轻不年轻,但说多老也谈不上,虽然郝新是男人过去的徒弟,但终究男女有别,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只怕徒弟还没带成,流言蜚语早就如暴雨来临前的狂风,灌满大街小巷了。但他提出要求的时机,早不早,晚不晚,刚好就在向钥匙有了前一晚那场惊魂未定的遭遇之后,向钥匙就有些犹豫了。
向钥匙没有一口回绝,只说:“我先想想。”
向钥匙“想想”的结果,我们都猜到了:徒弟郝新留了下来。
郝新留下来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向钥匙意识到,果真在要开锁行里谋衣食,没有个男的,真不行啊。
郝新留下来继续当学徒。向钥匙慢慢就觉得,自己这个决定确实英明伟大。别的不说,单说夜里再碰到有人要开锁,那当然就是郝新出马,不必再让她一个弱女子像打仗一样东奔西跑,跟玩命似的。而她担心的所谓流言蜚语,居然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凶猛。也难怪,她比郝新大了足足十几岁呢。嘴巴再烂的人,就算心里有点别扭,看到两个人那么大的年龄差,也不好意思嚼什么。
再说了,谁规定女师父就不能带男徒弟了?
更何况,这个徒弟本来就是她男人先前的徒弟。徒弟回来一边继续学艺,一边帮师娘的忙,不都在情理之中吗?
不知不觉,三个月就过去了。这三个月,向钥匙是满意的。她甚至想,等郝新把艺学好,她可以让他留下来,给工资也行,分红也行,出门在外跑开锁那一套,可以全交给他。自己可以像男人在世时候那样,就在店里守着。郝新谋了份生计,虽不能大富大贵,但吃穿住用肯定是不用愁的,也肯定比他在外面像只无头苍蝇一样乱窜要强得多。自己也轻松,可以将更多的心思用在培养孩子上面。毕竟,孩子很快就要上高中。再不看紧点,只怕就废了。她可不想儿子再像妈老汉一样当个开匠锁!
这天,向钥匙像平常一样早早就到了楼下门市。晚上不出门,觉睡得好,精神就是不一样。郝新一般在八点半之前就会过来。但直到九点,还不见他的影子。向钥匙有点不悦,心想就算有事,也应该来个电话说明一下啊。艺还没学精呢,就想出师啦?好在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她又一想,也许是晚上熬了夜,睡过了头。再等等看。可是,左等右等,一个上午都快过去了,还是不见郝新冒头。向钥匙有点担心起来,会不会出什么意外?一想到意外,她就有点忐忑不安了。要知道,当初男人就是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中永远离开的呀。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慌乱。尽管她不相信,命运会一次又一次将她推到绝望的悬崖边。她努力把腰板挺直,定了定神。然后,她拿起了手机。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向钥匙把手机贴在耳边,就像贴着枕头睡觉一样,沉沉的,回不过神。
从那天开始,郝新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就那么凭白无故,没有任何先兆,没有任何说明,就从向钥匙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大约又过了半年。这天,向钥匙正在门市上闲着无事。也不知是不是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出门在外到处乱跑的人少了,所以忘记带钥匙把自己关在门外的人越来越少。也就是说,跟周围的小商小贩一样,向钥匙的开锁生意也明显受到影响。需要开锁的人少,她就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卖锁上。但买锁的人一样不像原来那么多。想想也是,大家一天到晚都呆在家里,哪还需要锁来挡“肖小之徒”呢?以前卖得很好的密码锁、电子锁、刷脸锁,也都不好卖了。钱越来越难挣呢,大家把心思都放在了挣钱上,而不是保财上。向钥匙正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就见两个精神十足的警察径直走进门来。
走在前面的警察到了向钥匙面前,问:“你是何桂碧吧?”
向钥匙好多年都没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了,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三四秒,才赶紧回道:“是是是!我是何桂碧。平时大家都叫我向钥匙。”说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警察也觉得有点好笑。居然有人会把自己名字都搞忘了的。但再一想,也在情理之中。警察脸上有了笑意,氛围就不像刚才那么严肃。前面的警察指着斜后方的警察说:“这位同志是从湖北赶过来的。有一桩案子,需要跟你核实一些情况。”
向钥匙脑子里“嗡”的一声响,不知道自己从没有去过湖北,为什么会有湖北的警察找上门来?更不知道自己向来胆小怕事,违法乱纪的事做梦都不敢想,为什么会有案子跟自己牵扯上?
那位湖北的警察上前一步,离向钥匙更近一些,说:“郝新这个人,你认识吧?”
向钥匙心里咯噔一下,她似乎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认识。他以前是我男人的徒弟。”她本想说后来也是自己的徒弟。但转念一下,还是算了,免得越说越复杂,越说,反倒越说不清。
湖北的警察转脸对另一位说:“这就对了。”
先前开口的警察显然是本地人,肯定是县公安局派来协助调查的,这时候说:“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有些事情,我们需要了解得更详细。”
从公安局大门走出来,向钥匙总算松了一口气。只要她知道的情况,她都毫无保留地向警察和盘托出了。但同时,她又始终觉得,心头就像压了块巨石,怎么用力想掀开,都掀不开。她觉得心脏被压得“砰砰”乱响,仿佛下一秒就会被压破似的。她怎么也想不通,看起来那么羞涩、腆腼的一个年轻人,怎么会跟偷银行保险柜扯上关系呢?别的不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监控视频、报警设施相相俱全,还想着去偷银行,不是傻到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就是一碰到关键问题脑子就发热,总以为万一运气好,得了手,一辈子,甚至下辈子就彻底翻了身。所谓“富贵险中求”,说的怕就是这类人吧。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郝新,出门在外的这些年,根本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在广东打工,而是成了个四处流窜作案的惯偷。前些年因为都是偷的寻常百姓家,又打一枪换个地方,所以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也掌握了一些证据,但就是拿不到这个具体的人,归不了案。这次倒好,他自以为神通广大,竟然胆大包天到去偷银行保险柜!然后,就被警察瓮中捉鳖,直接逮个正着。更让向钥匙冷汗直冒的是,你说他自己偏要往枪口上撞也就罢了,可差点还搭火烧铺盖,把她这个本本分分的弱女子也牵扯进去。
原来,郝新闯进银行去开保险柜,用的居然是向钥匙男人生前的“钥匙”!当然,这里所说的钥匙,并不是像人们平时所见识、所理解的钥匙,而是一种特殊的工具。这种工具市面上从来没有得卖,都是技艺高超的开锁匠根据经验自制的。制作出来,也知道很难用得上,不过就是图个虚荣。你看我多厉害,银行保险柜,我都能打开!向钥匙知道男人有这套工具,也知道男人曾经真的用过这套工具。每每在她和郝新面前讲到那次开锁经历,男人脸上都浮现出无限的荣光,仿佛能把银行保险柜打开,就跟战士上战场杀敌,直接一枪摞倒敌方阵营最高指挥官一样。那种感觉,别提多爽,多妙,多开心!但男人开银行保险柜,跟郝新开银行保险柜有本质的不同。男人去开,是那个镇上的银行工作人员不知什么原因,竟然忘记了前一天刚设置的密码,怎么打也打不开。最后不得已,才向开锁匠求助。但开银行保险柜,并不是所有的开锁匠都有的本事。整个新县城,一个一个数,有这本事的,绝不会超出三人。
但向钥匙跟男人在一起的那些年,男人再也没有机会用那套特殊的工具了。时代在进步,银行的保险设施也在更新,向钥匙不知道现在有多少银行还在用那种老掉牙的、需要手输密码的保险柜,但她相信,像那个镇上那样的银行工作人员,寻遍全国,怕也找不出第二个了。保险柜密码都能忘记,那心得有多大,得有多失职才能干得出啊。
可是,明明是男人的“钥匙”,怎么就到了郝新手里呢?一想到这个问题,向钥匙就觉得背脊一阵阵发麻。现在看来,一切都肯定是有预谋的。比如,那天夜里她出去开锁,都凌晨两点了,他怎么会刚好就在她楼下?他说他才坐长途车回来,可只是他的一面之辞。难道不会是,他早就在楼下的门市外面伺机而动?只是刚好见她出来,就临时改变主意,今晚不要行动,而要用一种更隐蔽、更稳妥、更手到擒来不会有任何闪失的方式去达到目的?他的运气也真是好,他跟踪了她,竟然真的让他碰上一个英雄救美的大好机会。然后,他再靠近她,甚至走进她的生活,不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吗?
之前想不通的一切,现在都想通了。包括他为什么要继续来当学徒,为什么连工资都不要,也愿意留下来帮她。他是在寻找机会啊。他知道师父有那样一套工具,但他不知道,师父把那套工具到底放在哪儿。不要说他不知道,就是向钥匙,也不是十分清楚。一辈子可能都用不上的东西,谁会关注、关心呢?
而一旦他的目的达到,就果断消失。
现在看来,他的计划是成功的。因为自始至终,他所做的一切,她都蒙在鼓里。如果不是警察找上门来,她都不知道男人以前的那套特制的开锁工具,竟然已经失窃了!
郝新这事对向钥匙的打击不可谓不大。首先是动摇了她对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感。她想不到,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为什么可以伪装得这么深?你所看到的善,可能是恶,你所相信的真,可能是假,那么,我们到底该信谁,或信什么呢?谁或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相信的呢?其次,也直接影响到她对待生活的态度。特别是在开锁这件事上,她不再像以前那么积极热情,人家电话一打来,就好像自家的房门被关了一样,生怕跑慢点,就生出什么意外来。现在,她就是把开锁当成个谋饭吃的工具,工具总是冷冰冰的,用得着的时候,拿起来,用不着了,扔到一边,完全跟自己没关系。当然,该快的时候,她还是会快。她的快,不再是急他人之所急,而是快点把这单跑完,钱一到手,又可以跑下一单。就好像,她要服务的对象,不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只是一串又一串阿拉伯数字,这些数字不再是电话号码,而是一张张人民币。
那天,她照例去开锁。她已经把摩托换掉了,买了辆外形酷似小轿车的电动四轮车。对一个女人来说,骑着那么大个笨重的铁壳子在街上跑,终归不安全。
到了那里,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正焦急地在门口的楼道里来回踱步,像只热锅上的蚂蚁,怎么转圈,都转不出被炙烤的命运。见开锁的终于来了,才长吐一口气,又将那口气深提上来,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急切地催促道:“快,快点!快点开门!”仿佛她动作稍微慢一点,马上就会出大事一样。
门是反锁的。
反锁的门开起来要麻烦些。但向钥匙毕竟是向钥匙,她没有辱没男人留给她的好名声。很快,手底下有了那种突然“咯嘣”一下,松驰下来的感觉。她知道,锁开了。
她刚把门轻轻一推,旁边的男人一个箭步冲上来,“砰”的一声就将门踹了出去。这突如其来的一脚,惹得她不由自主地朝屋里一看。那一瞬间,她觉得她的整个人顿时凝固在了那里,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血液流动。
这怎么可能呢?她开了那么多年的锁,从没有见过眼前这一幕:一个女人,穿着薄薄的一袭睡裙,像条沙袋一样吊在客厅中央。身子还随着头顶上方的吊灯在空中晃来晃去……
女人没有死。
男人将女人放下来,只在女人胸口按了几下,女人就轻咳一声,微睁了眼。那一刻,向钥匙却没有丝毫松驰下来的感觉,反倒觉得全身像被无数条绳索捆绑着,不断收紧,收紧,再收紧……她真想跑到某个无人的开阔地,向着空空如也的天际,大声喊叫几声,然后,埋下头,掩着面,痛哭流涕。一个问题,像条蛇一样纠缠着她的内心:如果,如果她跑得慢一点,或者在路上口渴了,把车停下来,在路边的小摊上买瓶水,喝完了再走,再或者,她那可怜的电动四轮车,跑到半路却没电了……眼前的情形,又会怎样呢?
向钥匙当然不可能马上就跑到想象中那个无人的开阔地。她在一旁协助男人将女人扶到床上。从男人追悔莫及的自责声里,从女人虚弱无力、断断续续的控诉中,她终于拼凑出整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女人发现男人在外面有了小三,一大早,就找男人扯皮。两个人大吵一架,男人不堪其扰,甩门而去。等到中午男人回家,开门,门开不开,打电话,电话打不通,一种不详的预感突上心头,才有了后来向钥匙所见的一切。
从那户人家出来,向钥匙在背后轻轻一带,房门就锁上了。
她又想起了前些天一直在心里折磨她的问题,门轻轻锁上那一刻,她仿佛有了自己的答案。是的,有时候我们确实不知道该信谁,但至少我们还可以信自己。我们也的确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相信的,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样简单的至理名言,一定是值得相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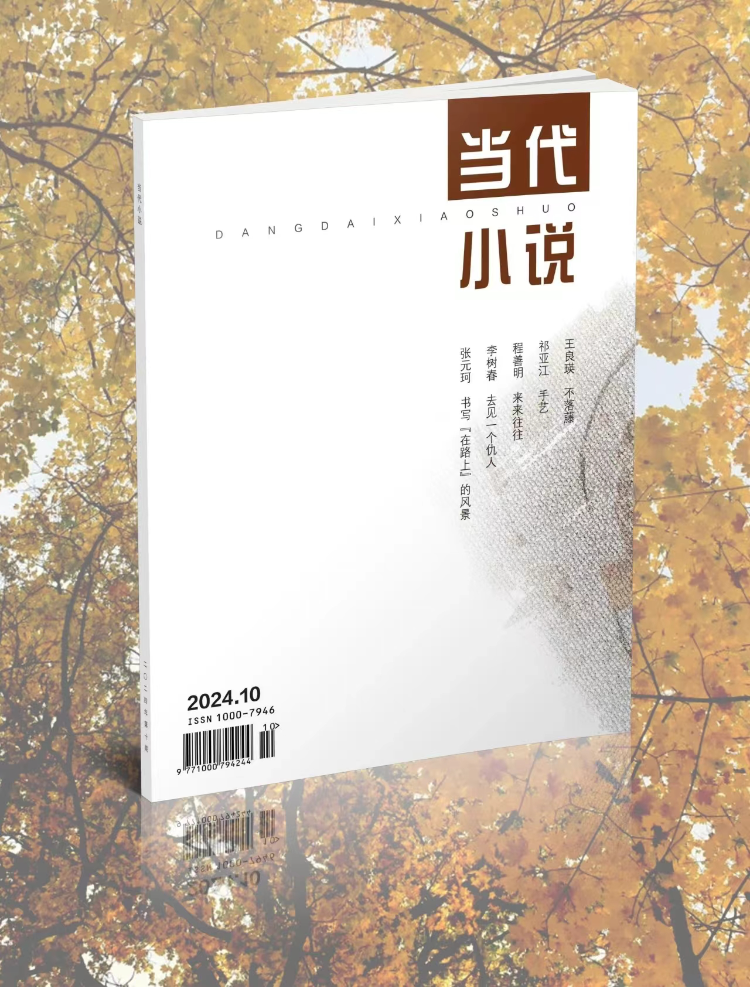
(原文刊发于《当代小说》2024年第10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