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丨刘泽安:鱼道 推荐丨刘泽安:鱼道

鱼道
文/刘泽安
清溪村有一座寺庙,寺庙不大,倒也整洁干净。奇怪的是寺庙前的一块石头上刻有一条鱼,活灵活现的,尽管风雨剥落了几十年,其形象依然栩栩如生。
清溪村边有一条大河,河真的是宽,一条古老的大坝横亘在河上。据说,这条大坝修建于民国时期,说古老也不古,也还真看不出老的痕迹,那青而带白的条石,既有一丝丝的光滑,又有环环相扣的紧凑,三块条石一米的厚度,一块连着一块稳稳当当地坐在河中。一年大部分时间,大坝上是没有水漫金山的样子,只有汛期才是水涨淹坝,大的时候,水是翻着浪花唱着歌急速翻坝而下,鱼儿也随浪花漂下,胆子大的人也不敢去破胆尝试过坝。水小的时候,轻轻地缓缓地从坝上流过,过河的人们尚可蹚水而过,胆子小的就在水淹的大坝上一步试着一步,那真的是走一步试一步,过了河上坝的那一瞬间,还在为自己顺利过河而庆幸。其实,这点翻坝水对河两岸的村民来说,那是小ks,根本不值一提,连我这样的小孩子都不怕,一步一个脚印地顺利过去。
我的家就在清溪村的河边,离河岸相对较近的缓坡上。房子为什么建在缓坡上?当然是为了防洪水,大河大部分时间是温柔的,一年也有那么一小部分时间像猛兽一样肆无忌惮地掠夺两岸的村庄,两岸的村民建房都要考虑比河水常年的洪水位高一些,以防被河水淹。我家的二层小洋房在村庄也不算显眼,小洋房虽谈不上比比皆是,但不少的人家都是。
我原来在村里的小学读书,一直读到四年级,学校撤了,只能到镇上的中心校去读书,一周回家一次。回家就要过这条大河,大河上的一条驳壳船比一般的船要大,可以坐十多个人,每人一块钱,妈妈给了船钱,不想我去走大坝冒险。我一点不怕,大多是过船闸走大坝,常事,既节约了钱,时间又快,一顺溜就过去了。走船闸要小心一些,因为闸很窄,两边又相对高一些,人一滚下去全是闸的深水潭,大坝宽许多,只要水不漫上去,我都是走闸和坝回家。偶尔大河涨水了,只要不封渡,我也愿意过船。坐船也有不少的乐趣,看船老大推,自己也想上去尝试,撸啊撸,看大河的浪花飘,常常能清晰的看见各种鱼儿水中游,跟着船游得不快不慢,完全没有把船和船上的人看在眼里,如果坐在船边,还可以用手在船弦边捞呀捞,尽管捞不到水里的鱼儿,那样的戏水有趣,坐船的孩子都喜欢。现在的船又不一样,是机动船,不用人工使力划,轻轻的开动机器,船就向对岸驶去,不过船顶上冒黑烟,“噗噗噗”的声音响起在河水上有些惹人烦,大人小孩说句话都听不清楚,要处在耳朵边大声地说。也因为如此,坐船过河的人越来越少,走闸和大坝的大人小孩越来越多。
学校放周末假了,我要回清溪村的家,在路上同行的同学是夏天。坐车下了后,我们商量先到什么地方玩一玩才回家。
“青乐,我们不走渡口,去闸坝走走?有一个惊喜告诉你。”夏天问我。我睁大眼睛看着夏天,他可很少这样的,跟他去一趟闸坝看看,听听有什么惊喜?
我叫青乐,已经是镇中学七年级的学生,夏天是我的邻居,我的同班同学。我的妈妈外出打工,爸爸在家,夏天的爸爸外出打工,妈妈在家,都算是半边留守儿童,大人没时间管我们,放了学就是我们自己的天下。
我们的天下也不宽广,前后左右也就那么巴掌大的地方,有山岗岗上绿色的树林,也算不上森林,有山坡坡上稀稀拉拉的庄稼,长得好与不好也没人关心,有山湾湾里那浅浅的池塘或者水田,包池塘养鱼的、自家种水稻的倒好一点,有人常来池塘的田坎走一走,看一看池塘里跳跃欢快的鱼儿,鱼儿一跳去场镇上,换来的就是一沓沓的钞票。种水稻的则不一样,一年就等那一季,数不尽的春夏秋里耙田、栽秧、挞谷的日子,换来的钞票要薄许多。这也不会惊扰我们在田野里的快乐。
走走闸坝也是一种快乐。我和夏天就穿过渡口的码头。码头的那棵大黄葛树是我们的老朋友,常年的绿叶和宽大的树枝丫为码头等船的人们遮太阳挡风雨,落叶的时候,粗壮的树杆也是威风凛凛,生长的枝丫伸到河水的上空,遮住了岸的凋零,特别是黄葛开花那一段时间,香了一河两岸。每一次过码头,我和同学们都会爬上黄葛树上玩一会,不耽误坐船,船一到岸“咚”地一下子跳下来,船没到就在黄葛树的大枝丫岔口里歇一歇,听一听鸟语,吹一吹河风,惬意得很。
我和夏天往闸坝走去。心里的疑问没有解开,夏天要给我的惊喜是什么?我知道老家的这个闸坝不是一般的过船闸坝,有一段不同凡响的故事,也没有人详细跟我们讲过。只是隐隐约约地晓得一些简单的事,大多数时间闸坝就是个闸坝,跟我们村庄的树花草庄稼差不多,但一当有人专门提起它,我们的心里又有一些异样。
从码头过来一截小路,路上有一座短的铁索人行桥,桥面不宽是木板,够两个人挤着平行行走,如果是第一次走的话,看着下面还有点恐慌,当然啦,对我和夏天来说,这也是个小ks啰,常常走,看都不用看上下,目不暇接的走过去。桥下是大河的一部分,一条引水渠就从这儿把大河的一部分水分流到了一座小发电厂。过了铁索桥,两座四合院式的房子,有点乡村别墅的风格,是闸坝和电厂的办公楼,两岸村庄人们崇拜里面进出的人,那是一个个的铁饭碗啊。四合院的外边,与乡村没有什么区别,一小块一小块不规则的土地上种满了乡村中最常见的蔬菜水果,被围在村庄里的四合院也是村庄的一部分。
看见了闸坝,船闸边有几个人在那里指指点点说着什么,又在两个闸之间走来走去。
“青乐,你看那船闸跟以前不一样吧?”夏天问我。
我再看了看,说:“不只是多了几个人吗?”
“人是多了几个,也打破了平常的宁静,好多年没有这样的热闹了。”夏天的话中有话。
那倒是,大河上的闸坝和船闸都是宁静的,除了过河的人和过闸的船,没人来看,没船来行。水是径直往前流去长江不回头,更多的人则离开两岸村庄,一首民歌里唱着:
船还是那个船,
闸还是那个闸。
大河涨水浪沙洲,
无人来看河涨水,
无人来看河行舟。
船也不是那个船,
闸也不是那个闸。
一河浪花岸凋零,
一棵黄葛树啊,
照看这副模样的村庄。
这几年的村庄慢慢的枯萎着,像一朵花凋谢一样,这样的闸坝和船闸也如此,船不过了,过的人也少了,曾经热闹的大河也清静了。
“天,天,快过来。”船闸那边的一群人中有人喊夏天,夏天像是早有准备一样,拉着我快走几步,就到了船闸旁边。
喊夏天的人走过来,是一个中年男人,发际线特别高,头发又从中间向两边分开,一头浓浓黑发,有点中年油腻大叔的样子,精神状态尚好。
夏天把我推到前面:“浩叔叔,这是我最要好的同学青乐,他特想了解这座大坝和船闸的故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向浩叔叔点了点头,算是认识了。夏天接着告诉我:“浩叔叔是这个闸坝管理站的站长,在这儿工作了十多年,最懂闸坝,凡是跟闸坝和船闸有关的事他都清楚。”
这个被夏天称为浩叔叔的人,在这个闸坝工作了那么久,我好像没见过似的。夏天是懂我的同学,知道我一直想把闸坝的故事弄清楚,就给了我这个机会。
“来,夏天,青乐,你们来看看今天的船闸。”浩叔叔招呼我俩。难道今天的船闸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想都没有多想,浩叔叔的一番话让我和夏天惊讶。
浩叔叔告诉我们老船闸要新生了。前几年,浩叔叔和海事处(管理河道运输的单位)的同志一起向上争取大河运输能力改造提档升级的项目,正值市里提出陆海新通道的概念,提高内河运输能力的事又重新提出,改造大河上的船闸及大坝迫在眉睫,一级一级的从长江口往上改造,要不了几年,这条大河便是黄金河道。特别让人们想不到的是要在大河上建一条一条的鱼道。
什么鱼道?夏天和我更是惊讶。
简单说就是让鱼自由畅游的通道。从上游去下游顺水而游,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你们也常常见一群群的鱼游走,可从下游往上游的鱼,你们看见了吗?有使劲儿地向上蹦的鱼,可有成功的吗?这些坝建了几十年近百年,大河的鱼种类是越来越少,上面说为了更好地保护鱼类的生态多样性,必须要考虑建设一条一条的鱼道,让鱼类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产卵,继而生存下来。
我还是不太懂,夏天问浩叔叔:“叔叔,不是给我们讲讲大坝的历史吗?鱼道的事还是没弄清楚?鱼不是在河里游得好好的吗?”
“这样,今天的时间紧,我还要陪专家们看上游的船闸和大坝。大坝的历史展览正在站办公室布置,一个月以后去看的话,就更好懂了。鱼道好懂,你们不是去那个发电厂的排水口里外弄过鱼吗?你们都叫那蹦跳的鱼是飞鱼吗?那往回跑的鱼就应该有一条鱼道。”浩叔叔边说边急匆匆地离开我们,去追赶那些专家的步伐。
原来夏天一直记住我曾经说过的话,书上记载大河大坝的事太简单了,想找熟悉的人介绍,看来今天不凑巧。不过,让我们两个同学眼前一亮的是有个鱼道之说,而且一下子就回到了那发电厂排水口捉鱼的场景。
那是夏天,真正的夏季,不是我同学的名字。我缠着在发电厂上班的小叔叔走进发电厂大门,跟门卫打了声招呼,没有那声招呼还真不行,发电厂的车间是重要场所,一般不允许发电厂以外的人进出。我有些飘飘然,去发电厂的排水口去看鱼捞鱼看飞鱼,那可是村庄里所有孩子的梦想,没有谁能抗拒,但能进去看的毕竟是少之又少。我是其中一个幸运儿,那是何等的好运气。
这个村庄边上的发电厂,那是神一般的存在。大坝建成后十多年,新中国成立了,为了更好地利用大河的水资源,周边的十多个村庄组织了几千民工在大河边挖引水渠,工地上红旗飘飘,上千人的劳动场面,他们不分男女地开挖水渠,开凿石料,修筑护坡,建设厂房,硬生生的把一坡坡的土地挖成了800多米长的渠道,活生生地把大河水引入发电厂房,解决了周边十多个村庄的生产生活用电。可发电就要排水,排水就是一道奇观,水喷涌着白色浓郁的浪花而出,电厂的工人和附近生活的村民渐渐地发现一个秘密,随着浪花出来的还有一条条的鱼,有大有小。
我跟小叔第一次去排水口捞鱼,是初夏的一天。那还是小叔告诉我排水口的秘密后,天天想去看。一个周末,太阳出来好大,小叔说天气对头,去准有收获,我和他提着一个大笼子,穿过厂房,沿着专用的楼梯去排水口。排水口不远处的大河两岸郁郁葱葱,开花的开花,葱绿的葱绿,村庄恣意生长的不单单是庄稼,也有鱼。
正值发电厂放水,水是浪花似的翻滚,太阳在大河上空火辣辣地照着河面,浪花中已经看见有鱼在翻滚,一条一条地在浪花里飞。小叔指挥我把挂在石壁上的网拿下来,慢慢地从石壁的铁环扣梯下去,一扣一扣的一只手拉着,另一只手抓着捕鱼网。等在下面的小叔接着渔网,使劲儿的往外伸出去,网的长度正好可以在排水口的浪花中从下往上迎着太阳光,那向上的过程就是迎着鱼进大笼子的过程,小叔的力气不错,一阵子,那笼子里中就装了几十条鱼,估计有鲫鱼鲤鱼草鱼好几个品种。我就充当小叔的帮凶,洋溢着笑脸把笼子里的鱼往早先准备好的桶里倒,一条鱼一条鱼的数来数去,并且不时地捞在手里看一看。没有多长的时间,大半桶的水里就装的全是鱼,鱼在桶里蹦来蹦去,跟大河的天地相比那是天壤之别的。我面对这些鱼,没有半点的羞耻心,看着它们在桶里的游动,不时地用手去碰触它们。眼睛最多的还是看着小叔在排水口边捞飞鱼的动作,那个动作在太阳光下晃动有些刺眼,浪花中飞出的鱼还是在飞,小叔撒网的动作不停,渐渐的小叔动作软了,那长时间的不停歇也让手承受不了,桶里的鱼也差不多满了,鱼活动的范围更是狭小,我知道小叔要休息一下,先把战果弄回家再说。
从排水口往回家的方向走,尽量地回避熟人,免得别人看见满桶的鱼。小叔用他魁梧的身材挡着我,并悄悄告诉我,中午再来一次。
“小叔,中午还有鱼捞?不是不再放水了吗?”我有些疑问。
小叔拍了拍我脑壳:“天机不可泄露。”
回家,脑袋里一直是鱼的影子,蹦蹦跳跳后又偃旗息鼓的鱼,鱼那祈求的眼睛里,好像有我的影像,说不清这种感受,它也是一闪而过。只不过盼的是中午有鱼摆摆吃,好像又什么也没有。
中午的太阳光更大,排水口两岸边的树都没有精神,我和小叔过去时,蹲在排水口里边的小天井。这个小天井是为检修排水口用条石修建的,几个人蹲在那儿休息一会,空间倒也不小。小叔在条石上拴了一个捕鱼网,随时可以放进那个小天井的水里。
我和小叔蹲了一会,外边的太阳光与我们无关,可它与河水里的鱼有关。小叔的眼睛一直盯在天井的水里,几乎是一动不动,他的眼睛仿佛是鱼的天敌,在排水口周边的鱼都逃不过他的双眼。我是一个鱼盲,跟着小叔的眼睛转动。
小天井的水在晃动,水的颜色渐渐变黑,水的波纹在慢慢扩散,我看见小叔的手在抖动。
“嗦,嗦”清脆的声音一下子响起,小叔扯掉捕鱼网上的绳子,网一下子掉了下去,恰恰把小天井的大部分罩住,天井里的水泛起波浪,有鱼在翻水。看来,小叔真的是电厂里捕鱼的高手,什么时候下网,什么时候收网,那都是有定律的,他完全能够把握住合适的时机。一网搜上来,七八条大草鱼跳也跳不起来,在软软的网里躺着,我想伸手摸一摸鱼儿,小叔用眼神制止了我:“不慌动,鱼一跳入天井里,再想捞它就费力了。”
我搞不清楚小叔的心思,把鱼放进木桶里,更没有去想为什么小叔把握捕鱼的时机那么准确,但心里的疑虑没有解除。
小叔空手,我提着木桶回家,鱼儿在桶里蹦跶得少了,实在是蹦不起来。这个时候,小叔才告诉我:“中午天热,鱼儿要游进小天井里歇凉,鱼儿一多水就变黑黝黝的,网一下去就稳稳当当的套住它们。何况鱼儿在初夏时,有些鱼要想游回原来生活的地方去产卵,由于没有专门的通道,就选择想从电厂的排水口往回游,就是鱼路或者鱼道,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大坝一修,鱼的回路就堵死了,渐渐地,时间稍长一点,大河里的鱼的种类越来越少。”
小叔的话通俗易懂,那时我没有记住鱼路和鱼道两个词,只是觉得原来心目中自由自在的鱼儿太苦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一天晚上,村庄的夜晚满天星星,星星下的我脑海里全是鱼儿蹦跳着往上跳的动作,那摇摆的尾巴鳞片光溜溜的,一跳一闪的,仿佛鱼儿在向我喊话:救救我,孩子。
我醒了,坐在床上再也睡不着。
从这一天起,我对到发电厂捕鱼的事兴趣不大,随小叔去的回数少了许多,心里总是被一条一条的鱼儿缠住,但有时候又禁不住小叔的吆喝声,自觉不自觉地又去了一次又一次,只是捕鱼的那种兴奋劲儿早没了。
现在听说在大河上建一条鱼道,供鱼儿返回故乡,既稀奇又兴奋。大坝建设了近九十年,从来没有想过鱼儿的故乡,鱼儿游下去了怎么回家?一条河的本意肯定不是这样的,河就是鱼儿的家,哪儿都是鱼儿的家,没有路怎么行呢?我以前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不是太深奥了,是没有想过。
我和夏天对鱼道的事感兴趣,也不影响我们对大坝的兴趣。浩叔叔讲的鱼道,什么时候建成还是个未知数,大坝可是的的确确存在了几十年。
过了十多天,浩叔叔给夏天带话,让我们去看看大河大坝的历史图片展览,就在管理站的办公室底楼。
我们约了好几个同学去看大坝图片展。一进这小小的管理站,一张不算大的海报吸引了我们,十几座横在大河的阶梯上,一座连着一座,虽然谈不上雄伟,但也是威武不屈地屹立在大河的身上。展览室的图片更加完整,这条大河上的大坝是抗日战争时期修建的,主要是给战时首都重庆的钢铁厂运输煤炭、铁矿而建,那是钢铁厂造枪、造炮必需的原材料,这条大河成了抗日战争的一条物资生命线,为最终的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浩叔叔给我们讲解,特别谈到村庄的那座寺庙。船队运输经过时,船老大都要专门去寺庙里拜拜菩萨,求它保佑船行顺利,又凑钱在寺庙前的石头上刻了一条鱼像,作为神一样地拜一拜,以求准时把物资送到重庆的钢铁厂,保证战时所需的煤和矿。
真的,这条大河上的一切都值得尊敬,包括大河里的每一条鱼。
我更加了解了大坝的历史厚重和历史贡献,又为鱼儿回不了故乡水而懊恼,究竟是谁的对谁的错?
不过,从今天起,我希望大河尽快修成一条一条的鱼道,让上下的鱼儿通行无阻。
鱼道,成了我的梦想,一生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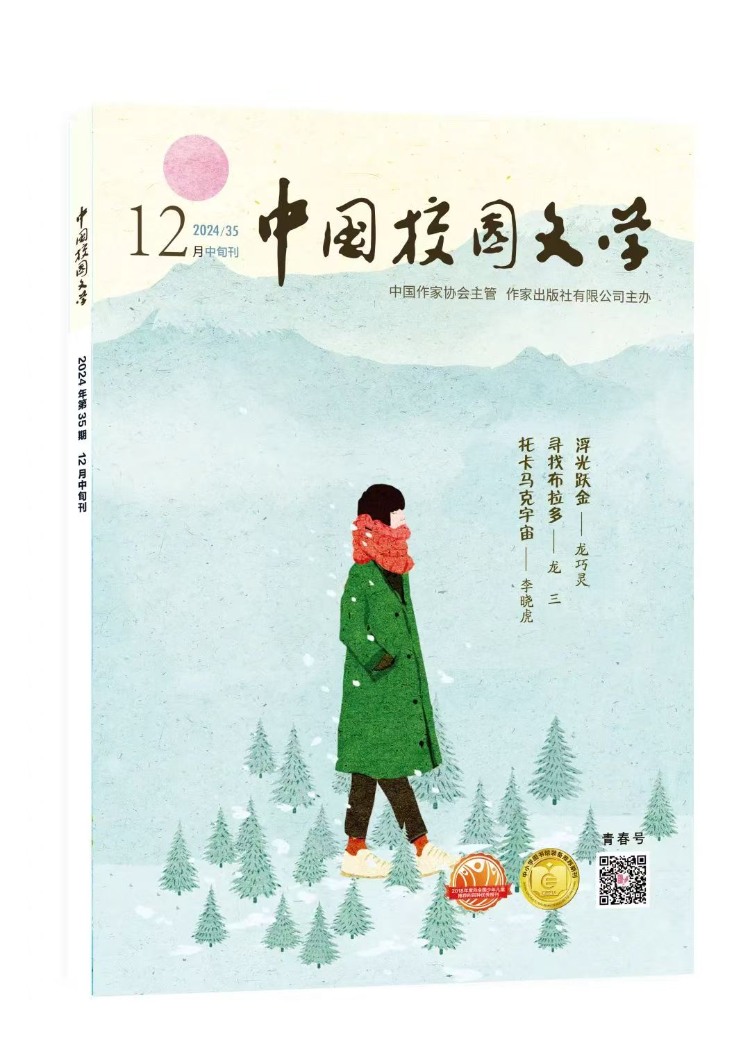
(原文刊发于《中国校园文学》2024年第12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