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丨杨不寒:昆明时序录 杨不寒小说 杨不寒

昆明时序录
文/杨不寒
春城之春
昆明的天气是独特的天气。春天是样板,秋天自不用说,夏天像春天,而冬天也像春天。
春天不用像谁,所以格外自在,有些不顾所以,终于把昆明这座城市弄成了“春城”。三月之初,春天就拄着它绿色的权杖驾临了。嫩叶花草从束缚中挣脱出来的瞬间,你可以听见权杖敲击出来的种种音节。柳条抽芽的声音像钧瓷在开片,桃李花开的声音分别像莫扎特和德彪西的曲子,海棠花开的声音是最烂漫的粉红,而松针刺破晴空的声音是冰凉且锐利的……
像是刚被校准的钢琴,每一个琴键都有力量要爆发出来。春天是一部交响曲,一整个剧场。走在街上的人们,如同身处于剧场之中。看着这座春天的城市,他们心里大概都会有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产生一点新的期许。就连颓废的人,望着出墙的枝条,也会愿意在这个季节把自己弄得更颓废一些。
春花实在开得太晃眼,太放肆,当地人只好含泪把它们吃掉。那天中午,我走出学校西门,去吃门口的一家菊花米线。偶然撞见一个中年人,举起手机对着一树玉兰拍照。抬眼去看,看见一只松鼠正抱着一朵紫色花啃食,眼睛滴溜溜地盯着我们,好像谁会去它爪子里掠夺食物一样。话说回来,昆明人吃花已经成为习惯,包括玉兰花在内,裹了鸡蛋和面粉,放在热油里一炸,蘸点辣椒面,就成为一道小吃。玉兰树是昆明的市树。昆明人对它的爱,真是爱得五脏六腑都是。
玉兰树边的这家菊花米线,就把菊花当作一味蔬菜烫进过桥米线里,增添了鲜香和一点情调。幸好陶渊明并不像他的崇拜者苏东坡一样是个老饕,什么都要放在锅碗里研究研究,否则南山的菊花恐怕都不能“托体同山阿”了。除了玉兰花和菊花,三月的山核桃花、四月的金雀花、五月的玫瑰花,以及芋头花啦芭蕉花啦石榴花啦虫草花啦等等,都在昆明人的菜谱里,排着队,等待被临幸。
沿着这家米线店,穿过文化巷,外面是沈从文和汪曾祺住过的文林街,继续往南走,或许还会路过闻一多遇难的西仓坡,接着就到了翠湖。按照汪曾祺的说法,翠湖不大不小,刚好适合游玩,这里的树都很高大,主要是柳树、桉树和香樟。翠湖的春天会种植一些郁金香,这是香艳而娇嫩的花朵,但也聊可装点现代人的生活。湖里那些从北方来过冬的红嘴鸥,陆陆续续都要离开了,但明年还会再来。
一直疑心翠湖和滇池的水是从哪里来的。昆明盆地向南的流水被高山阻断,盘龙河、邵甸河、金汁河、明通河在这里相汇。可这几条小河汇聚,当真能形成如此汪洋之势么。看来涓滴细流,真不可小觑。尽管有五百里滇池,二十公顷翠湖,昆明城却四季少雨,春天也没有什么雨水,每天都是艳阳与瓦兰色天空。于是,一切景物在视觉上都极富层次,色彩很饱和。在昆明老城区,我们很容易遇到一些古老的松树,这个季节都孕育出了新的松塔。无数鸭黄色的松塔,安详地端坐在绿色松针中,在阳光下看来,像是一幅色彩明亮的印象派油画。
除了松树,街头和云大校园里还多有龙柏,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的龙柏尤其繁茂厚实,其形象如同火焰,却周身都是冷静而沉着的墨绿色。我觉得这些树长得有些奇怪,总是要吸引我的目光和心思,好像要对我说出它们自己。但真实的情况莫非是这样——当我们带着诗性的感知走进春天时,万物都想要对我们说出它自己。
南国夏日
昆明给我这个重庆人最深印象之一,是这里种植了太多的仙人掌和多肉植物,并且这些仙人掌和多肉植物又长得那么高、那么壮、那么绿。春天的各样花朵落尽以后,这类植物的存在感便凸显出来,既表现出它们纯粹而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似乎在说明着昆明这座南方高原城市的夏日生机。
的确,在这南国之南,在这祖国西南最边陲的省会城市,夏日别有一种风情。且先放下那些可以当拴马桩的仙人掌不提,让我们把夏天从五月讲起。五月首先是蓝花楹的月份,千树万树,皆用干净而茂盛的蓝紫给昆明设色。盘龙江在圆通路的长段不过八百米,被种了将近四百棵蓝花楹,这时节一齐盛开,真有泼天的浪漫。再仔细去看,会看到一处处白色的斑点,像是用国画弹粉法弹到画卷上面的雪朵。把镜头放大,才知道原来那是站在树丛中的鹭鸶。它们骨骼轻盈,身子修长,时时陷在出神状态,像是得道者,或者得道者豢养的灵物。
几乎就在同时,翠湖里的荷叶也亭亭起来了,荷花从尖尖角到蓬蓬开,只在半个月之间。翠湖的荷花从五月一直开到九月,而最好的赏花期当在六月到八月间。绿漪亭上有四六式对联:风雨动鱼龙,池影碎翻红菡萏;丹青映楼阁,天光倒浸碧琉璃。红菡萏又碧琉璃,怎么看,写的都是翠湖的夏天。寻常日子都谈不上炎热,唯独猛烈的紫外线着实刺痛人的肌肤。于是,可以去到湖中的亭台或长廊下,随处坐坐。低头看,水底游着悠闲的锦鲤和蠢笨的王八。这时观察周围,必能看见一二闲人拿着面包或鱼食,一点点往水中投喂,耐心得像小说里忘乎所以的闲笔。
最近两年,每到八九月份,昆明也会象征性地热那么几天,很快也就凉爽下来。可见这里的太阳公公爱面子,可也知进退。反正在昆明,空调是几乎卖不掉的。昆明人在冬天买火炉也不是为了要取暖,而是为了煮茶和烤土豆、红薯、板栗和牛肉干巴。因为凉爽,也不怎么下连天的大雨,故而养成了昆明人爱户外聚餐的习惯。找几棵冠盖茂盛的大树,又或者搭上几个凉棚,就可以开始孜然辣椒地烧烤。烟火漫卷当中,一阵清风吹来,总让人精神一爽。不过,因为海拔将近一千九百米,昆明的温差很大,夏天尤其如此。白天出门时穿一件短袖,倘若一不小心逗留到晚上八九点,又没有外套可穿,就该领略那“清辉玉臂寒”的诗意了。
谈昆明的夏天,谈了半天都言不及意。其实呢,对当地人来讲,这个季节主要是拿来吃野生菌的!从几十块百来块一斤的松菌、虎掌菌、牛肝菌、青头菌,到成百上千的松茸菌、鸡枞菌、干巴菌,名目繁多,真如这个季节的星星一样不可胜记,都一股脑地被他们从大山里扫荡出来,或蒸或煮或炒或炸,最后送到五脏庙去超度。云南人爱生活爱得如此具体,一个菌子,被他们吃出了艺术性,吃出了仪式感。等到吃出了幻觉,吃进了医院,他们也不认为菌子有问题,只说是自己没有把它们烹熟。或许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地爱得盲目的事物。就譬如我老家川渝地区的麻将客,输得再惨烈,也断然不会怪罪那一百零八章麻将牌。就算在那些铩羽而归的深夜,躺在床上怄得睡不着觉,恨也只恨自己手气背。
翠湖秋色
湖水酝酿着秋天。秋天也围绕着湖水,波浪似的,层层叠叠地向周围扩散。直到把夏天的最后一丝火气,也清扫干净。等秋分以后,昆明便像被水洗过一样,整个城市都有了沁凉的触感。而满街的植物,尤其是香樟、银杏、鸡爪槭等乔木,也一天天地换上了更柔软的色彩。金黄的,嫣红的,葡萄紫的,斑斓而不耀人眼目。
不过,要最近距离地接近秋天,感受秋天,理解秋天,还是得回到湖边。二十五度左右的气温,当然适宜在翠湖边坐一坐,走一走啦。在翠湖的秋色里,无论是喝茶,还是喝咖啡,都能体会到那种世事苍老,而时光悠然的感觉。昆明人的生活,大都是慢悠悠的。一两杯咖啡,便可以坐在一张凳子上,消磨一整个下午。又或者和朋友围坐在一张茶几边,泡一壶普洱茶,同样可以不管时间的流逝,任由时代的发展,自在地度过三五个钟头。
正因为此,据说,在全国范围内,翠湖周围的咖啡厅,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算得上是一流水准。而饮茶的风气,同样是如此,沿着翠湖走一圈,随处可见名目各异的小茶馆。而翠湖中央的岛榭上,同样有招徕茶客的禅院。究竟是昆明人的习惯造成了这样的城市景观,还是这样的城市生活培养了昆明人的性格,实在难以判断。又或者,二者本来就在相融的又脉脉互通,彼此间都是离不开的。
而天空中的云朵,同时也是湖水中的云朵,更助长了这种看淡世事无常的地方性情。明人杨慎曾戍云南三十余年,所著《南诏野史》载:“汉武帝元狩元年,彩云见南中,在今大理府赵州之白崖,云南之名始此。”同为明人的谢肇淛曾撰《滇略》,亦载:“汉武元狩间,彩云现于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之名始此。”相关记载纷纭繁多,无非强调了地上的云南与天上的云彩间的关系。因为地处云贵高原,昆明的天空无比清朗旷远,而云层距离人尤其近。这些低垂在头上的云朵,简言之大抵是形态厚重,层次分明,且又被瓦蓝的天空衬托得格外洁白,有时候甚至白得刺眼。
我故乡三峡地区的云,也身负美名,所谓“朝辞白帝彩云间”“除却巫山不是云”“瞿塘峡口水烟低”,皆是诗证。只是三峡的云,过于高远寥廓。当其低下神女的身段,缠绕在群山之间时,又只能称之为烟。作为一个负笈昆明的重庆人,刚到昆明时,便被当地的云给吸引了。在翠湖边仰着一个脑袋看时,就想起抗战时期,沈从文寓居昆明,曾写过一部题为《云南看云集》的散文集。此公故乡湘西有山有水,常年亦烟亦云。那些烟云景致,总体上属于灵秀一路,知名文学形象“翠翠”就是这灵秀景致的人格化身。昆明城头的云则如大家闺秀般明亮利落,和沈从文故乡的云大有差别,大异其趣,无怪乎他会在《云南看云》一文中写道:“云南特点之一,就是天上的云变化得出奇。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云的颜色,云的形状,云的风度,实在动人。”
与其它季节不同,秋天的云别有一种从容闲适的意味。天空疏落,阳光柔软,人的心情也因为节令而清凉下来。这时坐在翠湖边看云,真有种黄金不换的超然感。那些云呆在天上,还嫌不够丰富,还要把自己映在水里,去争得一份空明蕴藉。尤其是暮色里,云霞如烧如焚地扑在水中,别有一种悲壮之美。那些云从一种形体变作另一种形体,从东边飘去西边。“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其间聚散随缘,变化万千,往来不定。但这一切都发生得很缓,演化得很慢。可是,水里的云却突然间动起来了,突然间裂了碎了,又突然间发出了惊讶的叫声——哦,原来是一只鹭鸶点水而过,像一团小小的白云,飞上黄葛树梢头去了。
你大可以继续坐着,也可以因为鹭鸶的一掠,而被感染得动起身来,沿着阮堤或唐堤,越过文津桥、九曲桥或定西桥,进入翠湖内部的诸多岛榭去看一看。翠湖里种植的植物,大多是不怎么落叶的热带、亚热带植物。但秋天,也会有许多红叶抢眼地冒出来。譬如乌桕、枫香、红叶石楠和红花檵木,都在这个季节,交出了体内温热的染料。它们配合着亭台红色的墙柱与鎏金的顶子,把整个翠湖点染得一片恬淡,一片温情,恰似萧索季节里的一盏盏橘灯。
可惜燕子桥东头那半塘荷叶,在天光云影中,一天天地憔悴了颜色,像是夏天穿旧了的绿罗裙。荷花是早开尽了,莲蓬也差不多干枯了。李商隐的佳句“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端的有一种雅人深致,然而这在昆明却是行不通的。昆明少雨。夏秋之际,偶有阵雨。唯独那雨点,总是黄豆豌豆般大小,一下便下得铺天盖地,其中绝无一丝淅淅沥沥的病态风情。这些翠湖枯荷所可能蕴含的美学呢,或许仍在等着一个痴人去发现,去发明。
昆明冬景
对北方人来说,昆明倒是四时皆可看的,因为这里的四时风景皆与北方不同。但对于南方人来说,尤其是对贵川渝等西南地区的人来说,最应该到昆明的季节,还数冬天。
十一月以后,到处都冷了起来。北方干冷,寒风像得了失心疯一样不知疲倦,在长街上嚎叫着跑来跑去,踢起一阵阵大雪;南方湿冷,空气里水雾蒙蒙,温度很少到零下,可所有的冷冽似乎都在往人骨头缝里钻,于是我常常想起一个词叫沁骨。尤其是重庆,冬天跟泡在冰水里没什么两样。不过,处于南国之南的昆明却不这样,它干燥,温暖,并且在一年末尾仍然明亮如新。除了温度会稍低一些,冬天的昆明在天气上和别的季节并无太大不同。正因为并无不同,所以显得足够奇怪。
到了十一月下旬,就开始陆续有红嘴鸥飞抵昆明。滇池、翠湖、盘龙江以及昆明其它河流湖沼,都是它们南北迁徙的重要集聚点。至于它们的老家究竟在哪里,没人说得清。这些白色军团,会安安心心在昆明过完冬天。等到来年春花乱开,大概四月份的样子,便又往北飞,最远能一直飞到北极去。这些一生都在赶路的族类,真是活得辛苦。
好在昆明人不仅自己懂生活,愿意在冬天支起个小火炉来烤土豆、红薯和建水小豆腐吃,而且还格外溺爱红嘴鸥。谁都愿意花上十块钱,买一袋饲料,在水边去喂食。就连来昆明旅行的人,也把红嘴鸥当作一种可以互动的风景,手举一片面包等着被它们叼走,还高兴得像占了便宜。大概便是为此,近些年,来昆明过冬的红嘴鸥越来越多。十二月过后,整个翠湖都铺满了这些白色的家伙,仿佛是水面长出了羽毛;一旦动起来也总是百十只飞成一片,远远看去,如同谁在水中扯起了一面白色的帆,整个翠湖都要被风吹走似的。
不过,等日头暗下来后,可休想再看到一只红嘴鸥了。据说它们会飞身而去,分散栖息在滇池边,等天亮后,再度进城来讨食。提及天色,哪怕在冬天,昆明的白昼也长得要命。早上六点出头天就亮了,晚上七点钟左右,这座城市才不甘心地落下夜幕。传闻维特根斯坦老兄不耐烦读书写作,只喜欢月亮,因为太阳出来了就得翻开书、拿起笔。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昆明的冬天,毕竟这里的天空,还算有他偏爱的那种明晰感。
明晰是因为身处高原,阳光好,紫外线强,因此也就很适合摄影。偶尔我走出校园,在文林街兜一圈儿,就看到满街都是凹造型的年轻人。除了这些网红地,云南大学校园里也会有很多人来打卡,在那条臭烘烘的银杏道上拍照。瓦蓝瓦蓝的天空,金灿灿的银杏树,更有阳光透过枝叶,投下一地碎影。若有忙着积攒冬粮的小松鼠从树梢跑过,地上的碎影便跳跃起来,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光阴里弹奏巴赫的《十二平均律》。落叶铺就的大道悠长而开阔,构成一幕暖色调景深,简直像是欧洲文艺电影的镜头。
这条银杏道,就在我宿舍门口。刚来这里念书时,我专门写过一首《银杏大道的冬天》,试图在语言中感应自己从无数条人生道路,走到此时此地的神秘因由。哎,听起来,我住在这里还算不错,是吧?可事实上,云南大学在很多方面都让我喜欢,唯独这里的学生宿舍却是全天下最糟糕的。它像一所监狱,设施粗陋,并且被管理得教条又愚蠢……除了这些形容词,没有什么值得继续说的。之所以还软弱地住在里面,主要是因为它廉价,而我呢,正好贫穷。说到这里,我心情都坏了,不想再写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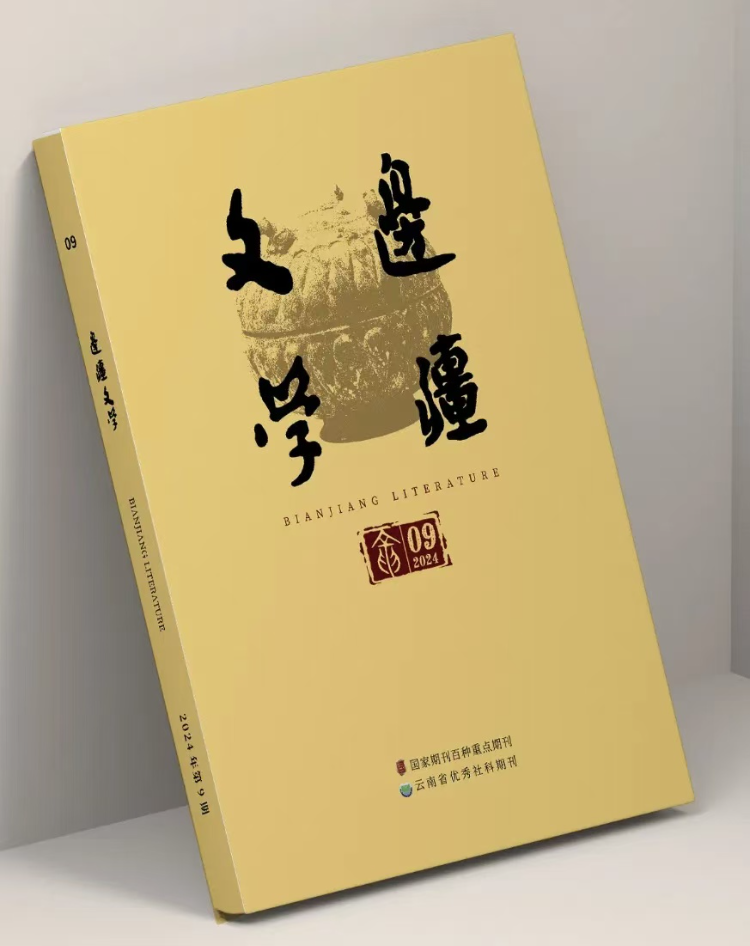
(原文刊发于《边疆文学》2024年第9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